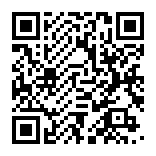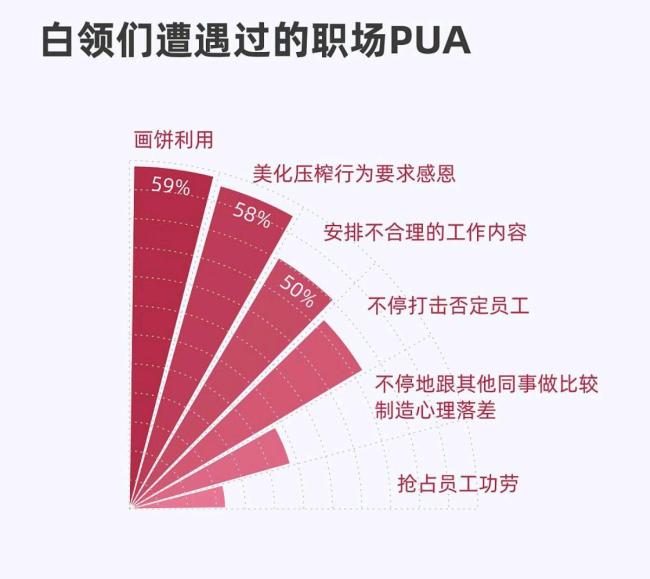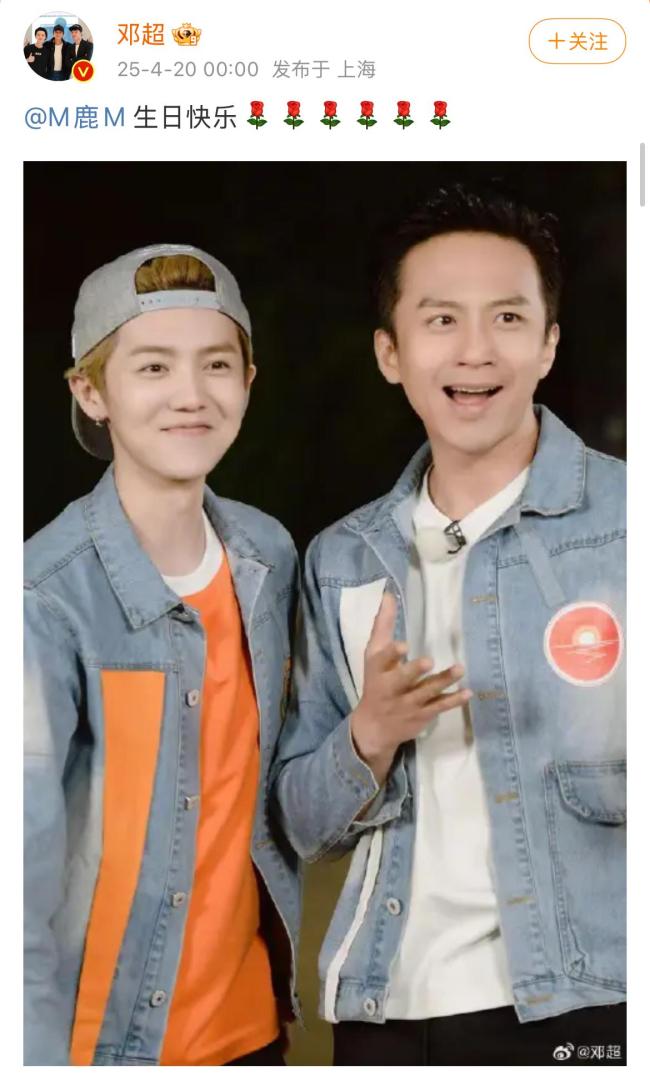大V:特朗普低估俄烏局勢復(fù)雜程度 單邊行動(dòng)難奏效
特朗普低估俄烏局勢復(fù)雜程度 單邊行動(dòng)難奏效,!2025年4月18日,,美國國務(wù)卿盧比奧在巴黎與歐洲國家及烏克蘭會(huì)談后發(fā)表聲明,,稱若未來數(shù)日內(nèi)俄烏和談未取得實(shí)質(zhì)性進(jìn)展,,美國將終止調(diào)解努力,。特朗普在白宮新聞發(fā)布會(huì)上公開支持這一表態(tài),。

不到三個(gè)月前,,特朗普曾宣稱“二十四小時(shí)內(nèi)結(jié)束俄烏沖突”,,但這一豪言壯語很快變成了笑話。這不僅是特朗普個(gè)人的恥辱,,也暴露出美國對外政策的功利主義傾向,,反映出其團(tuán)隊(duì)在國際事務(wù)中難以克服的結(jié)構(gòu)性矛盾。

歷史上,,美國能夠成功調(diào)節(jié)沖突往往依靠盟友的幫助,。冷戰(zhàn)后的國際沖突調(diào)解史顯示,美國主導(dǎo)的和平進(jìn)程通常依賴跨大西洋聯(lián)盟的共識,、國際制度的合法性背書以及軍事威懾與經(jīng)濟(jì)援助的雙軌策略,。從1995年代頓協(xié)議到2015年伊朗核協(xié)議,,歷任美國政府即便采取單邊行動(dòng),仍會(huì)通過北約協(xié)調(diào)機(jī)制維持歐洲盟友的戰(zhàn)略協(xié)同,。

然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交易型外交”打破了這一傳統(tǒng)。其單方面承認(rèn)克里米亞現(xiàn)狀的試探性言論(2018年),、反復(fù)威脅削減對烏軍援(2019年)以及公開質(zhì)疑北約集體防御條款(2020年),,導(dǎo)致美國作為中立調(diào)解者的信譽(yù)嚴(yán)重受損。這種歷史連續(xù)性的斷裂,,使得俄烏雙方均對美國的調(diào)解動(dòng)機(jī)產(chǎn)生懷疑——莫斯科視其為缺乏戰(zhàn)略定力的投機(jī)行為,,基輔則擔(dān)憂成為“棄子交易”的籌碼。

特朗普的商業(yè)背景塑造了其獨(dú)特的“交易藝術(shù)”外交風(fēng)格,,核心特征是短期利益最大化,、談判姿態(tài)不可預(yù)測性以及協(xié)議本身的媒體曝光度優(yōu)先。這種風(fēng)格在處理朝核問題等雙邊博弈中或許具有戰(zhàn)術(shù)價(jià)值,,但在涉及多邊利益,、歷史積怨與領(lǐng)土主權(quán)的俄烏沖突中卻適得其反。特朗普要求烏克蘭政府“展現(xiàn)靈活性”的表態(tài),,本質(zhì)上是用房地產(chǎn)談判思維解構(gòu)地緣政治矛盾,。當(dāng)國務(wù)卿盧比奧設(shè)定“48小時(shí)評估期限”時(shí),這種做法既忽視了俄羅斯對戰(zhàn)略緩沖區(qū)的剛性需求,,也低估了烏克蘭維護(hù)領(lǐng)土完整的民族意志。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對“高調(diào)撤出”策略的偏愛(如退出《巴黎協(xié)定》《伊朗核協(xié)議》),,使得沖突雙方始終懷疑美國承諾的可持續(xù)性。
自2017年“美國優(yōu)先”原則確立以來,,特朗普政府逐步解構(gòu)了二戰(zhàn)后美國主導(dǎo)的自由國際主義秩序,。這種價(jià)值觀轉(zhuǎn)向在俄烏沖突中表現(xiàn)為三重矛盾:對人權(quán)話語的選擇性使用削弱了支持烏克蘭的道德正當(dāng)性;對歐洲能源自主權(quán)的干預(yù)(阻撓北溪2號項(xiàng)目)暴露出利益至上的實(shí)用主義,;對國際法的工具化態(tài)度使得美國難以在頓巴斯地位問題上建立公正仲裁者形象,。當(dāng)盧比奧強(qiáng)調(diào)“重新分配戰(zhàn)略資源”時(shí),實(shí)質(zhì)是將烏克蘭危機(jī)置于大國競爭框架下考量,,這種價(jià)值觀的功利主義轉(zhuǎn)向,,使得美國既無法獲得全球南方國家的道義支持,也難以維系西方陣營的內(nèi)部團(tuán)結(jié),。
美國調(diào)解能力的弱化與其綜合實(shí)力相對下滑密切相關(guān),。經(jīng)濟(jì)層面,截至2024財(cái)年,,聯(lián)邦政府債務(wù)/GDP突破120%,,制約了對烏長期援助能力,;軍事層面,海軍艦艇數(shù)量降至冷戰(zhàn)以來最低水平,,難以同時(shí)在印太與歐洲維持戰(zhàn)略威懾,;軟實(shí)力方面,皮尤研究中心數(shù)據(jù)顯示,,美國國際形象在57個(gè)國家中的認(rèn)可度較2016年下降12個(gè)百分點(diǎn),。這種實(shí)力變遷導(dǎo)致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采取“成本外化”策略:通過施壓歐洲增加防務(wù)開支、推動(dòng)烏克蘭接受領(lǐng)土讓步來降低美國投入,。然而俄羅斯在能源武器化與核威懾升級方面的反制,,使得美國的“極限施壓”手段難以奏效。
俄烏沖突本質(zhì)上是一場嵌套在歐亞大陸權(quán)力重構(gòu)中的多維度博弈,。對俄羅斯而言,,這是維持其大國地位的最后紅線;對歐盟來說,,關(guān)乎能源安全與戰(zhàn)略自主的平衡,;對美國而言,則是維系全球霸權(quán)關(guān)鍵支點(diǎn),。特朗普政府試圖以“速成協(xié)議”打破這種僵局,,卻忽視了各方立場的不可通約性。俄羅斯要求具有法律效力的北約停止東擴(kuò)承諾及對其占領(lǐng)烏領(lǐng)土的主權(quán),,烏克蘭堅(jiān)持恢復(fù)1991年邊界,,歐盟謀求能源供應(yīng)多元化與美國安全承諾的綁定,這三個(gè)相互矛盾的目標(biāo)在現(xiàn)有博弈框架下難以調(diào)和,。
當(dāng)美國將調(diào)解與“印太戰(zhàn)略資源分配”掛鉤(盧比奧4月聲明),,實(shí)際上是將烏克蘭危機(jī)工具化為與東大競爭的籌碼,這種戰(zhàn)略焦點(diǎn)的離散化進(jìn)一步削弱了調(diào)解努力的可信度,。特朗普政府調(diào)停俄烏沖突的失敗,,本質(zhì)上是“美國優(yōu)先”范式與21世紀(jì)多極化現(xiàn)實(shí)的碰撞。在歷史經(jīng)驗(yàn)失效,、價(jià)值觀重構(gòu),、實(shí)力相對衰退與地緣政治復(fù)雜化的復(fù)合作用下,美國既缺乏充當(dāng)公正調(diào)解者的道義資本,,也喪失了構(gòu)建可持續(xù)和平方案的物質(zhì)基礎(chǔ),。盧比奧“48小時(shí)最后通牒”所暴露的,不僅是某個(gè)政府的策略失誤,,更是單極霸權(quán)時(shí)代終結(jié)的縮影,。當(dāng)美國將國際事務(wù)簡化為商業(yè)交易時(shí),失去的不僅是解決特定沖突的能力,,更是塑造全球秩序的領(lǐng)導(dǎo)合法性,。這種深層矛盾或?qū)⒊掷m(xù)定義未來大國競爭時(shí)代的外交困局,。
相關(guān)新聞
大V:俄軍在庫爾斯克勢如破竹
2025-03-13 10:18:33俄軍在庫爾斯克勢如破竹大V:牛市大概率并未結(jié)束,,慢牛行情可期,?
2024-10-10 14:53:41大V:牛市大概率并未結(jié)束大V:能立竿見影提振信心的唯有股市
2024-10-18 15:05:41大V:能立竿見影提振信心的唯有股市大V:李在明若上臺必有大動(dòng)作 中韓關(guān)系走向成謎
2025-04-05 22:47:03大V網(wǎng)絡(luò)“大V”司馬南偷稅被罰超900萬
2025-03-21 10:21:39網(wǎng)絡(luò)“大V”司馬南偷稅被罰超900萬大V:以色列不信任敘利亞新政權(quán) 質(zhì)疑風(fēng)暴再起
2025-01-01 16:16:16以色列不信任敘利亞新政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