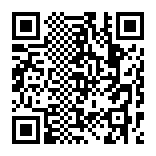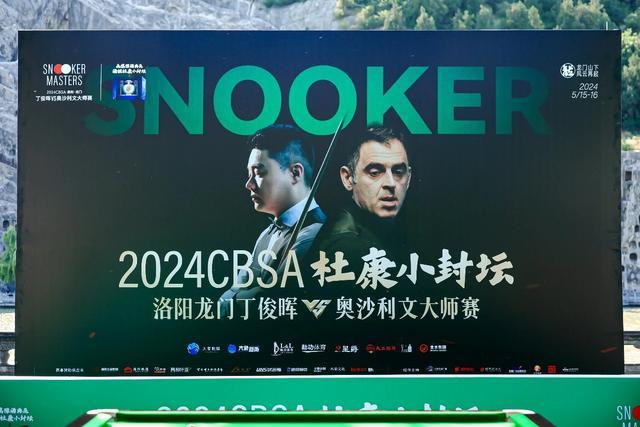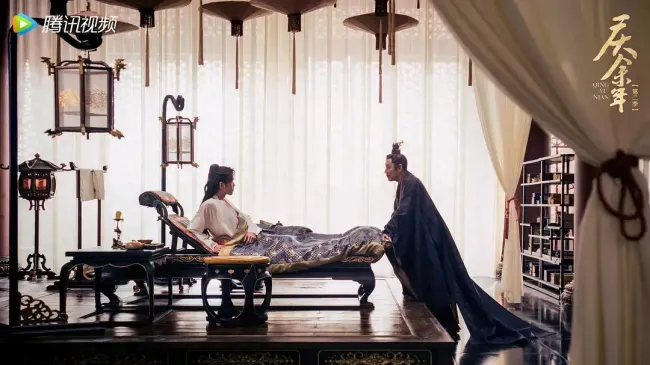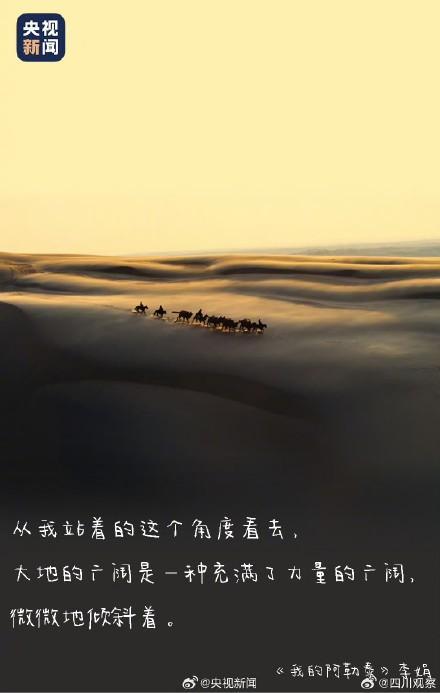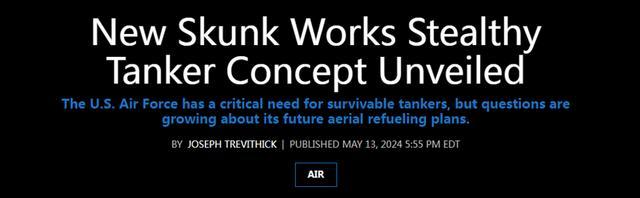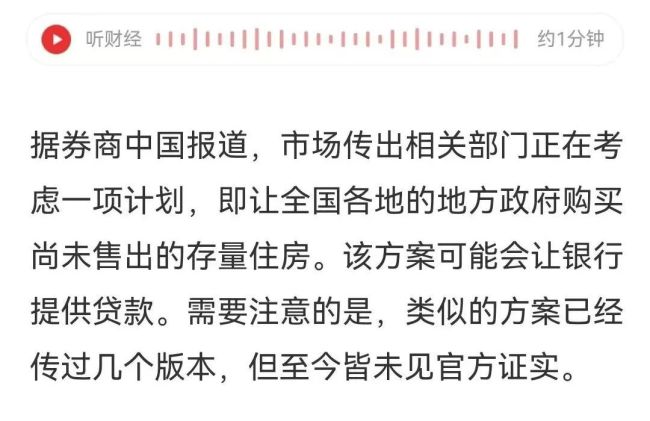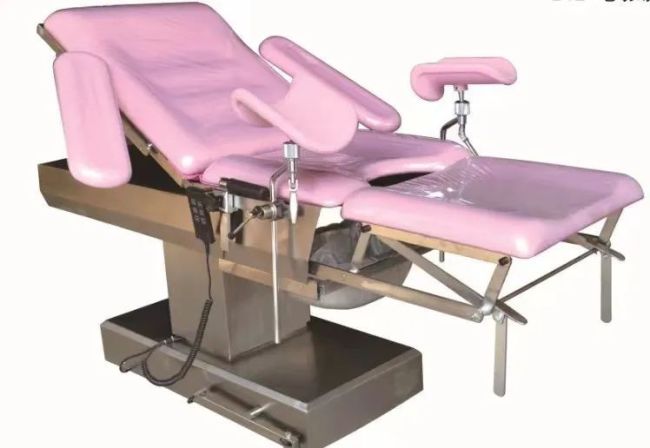學者:沮喪日增 俄烏沖突改變歐洲人的世界觀
烏克蘭危機不僅將改變歐洲的地緣政治格局,也正在改造歐洲人的世界觀。近期歐洲智庫和高校發(fā)表的一系列民調(diào)和研究報告表明,,令歐洲人驚訝且沮喪的是,,無論在對烏克蘭危機前景的看法上,還是在對當前國際秩序變化的認識上,,國際社會的主流民意與歐洲的主流認知大相徑庭。而且,歐洲所堅持的一些關于俄烏沖突性質(zhì)及出路,、減少相互依賴“去風險”以及兩極秩序必然性等觀念或原則,越來越難找到有力的邏輯支撐和現(xiàn)實依據(jù),,因此也難以得到其他地區(qū)和國家的積極正面回應,。這種現(xiàn)象會在進一步消解當前一邊倒的“挺烏反俄”政策合法性的同時,讓歐洲不斷產(chǎn)生“去中心化”的挫折感,,進而深刻地改造歐洲人的世界觀,。
首先是在俄烏沖突的性質(zhì)和出路問題上,歐洲發(fā)現(xiàn)有關沖突性質(zhì)黑白分明的判斷并非主流。歐洲以外的多數(shù)國家并不關心沖突的“道德性質(zhì)”,,也不接受歐美有關“烏克蘭不能輸,、俄羅斯不能贏”的目標。其中與歐美對立的觀點直指俄烏沖突已經(jīng)成為服務于美國全球戰(zhàn)略的“代理人戰(zhàn)爭”,,大多數(shù)民意也并不關心沖突能否達成政治解決,,而是以盡快停止沖突為最大訴求。
其次是歐洲發(fā)現(xiàn)盡管它仍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市場,、移民和旅游目的地之一,,但世界上多數(shù)國家的民眾并不那么認同或支持歐洲的價值觀和制度。這種被歐洲看作是“點菜式”的投機性固然令其深感不解但卻是最真切不過的現(xiàn)實,。
最后是如何在變局中找準自身定位并維護利益的問題上,,與由于要與美國保持政治立場一致而想在產(chǎn)業(yè)、技術上對中國搞“去風險”的歐洲不同,,國際社會多數(shù)成員并不拒絕反而樂意在與美國保持政治安全關系的同時,,與中國擴大經(jīng)貿(mào)合作和社會交流。這一認識分歧反映在更宏大的國際秩序變化方向問題上,,與多數(shù)歐洲國家設想的中美“兩極爭霸”場景不同,,國際格局的權力分化和世界秩序多極化的未來則更符合其他國家的預期。
俄烏沖突爆發(fā)在歐亞大陸的核心地帶,,它的延宕,、升級和外溢會直接威脅到歐洲的安全、經(jīng)濟和政治利益,,歐洲對其高度敏感并出現(xiàn)應激反應可以理解,,但想借此跟著美國樹立起“民主對抗專制”的二元敘事并向其他國家推銷,先從觀念上進而在事實上形成“兩極爭霸”格局,,顯然是高估了自己的“道義感召力”,,也低估了歐洲以外國家的道德判斷力。當歐洲睜眼看世界的時候,,會發(fā)現(xiàn)自身的歷史經(jīng)驗和道德感受不能替代其他地區(qū)和國家的獨立判斷,,自身與烏克蘭危機的利益關聯(lián)也難以換算成其他國家必須理解并支持歐洲的立場。更何況,,隨著俄烏沖突陷入僵局,、“烏克蘭必須贏”逐漸無望的形勢變化,歐洲內(nèi)部的分歧在擴大,、一些國家的立場也在動搖,。最近西方媒體羅列出“凍結沖突”“危機持續(xù)”以及“美國介入”這三種烏克蘭危機的可能出路,少了“唱高調(diào)”的激情,,多了回歸理性后的無奈,。這既是歐洲應激反應情緒逐漸消退的結果,,也是歐洲開始真正理性應對危機并冷靜尋找可行解決方案的開始。
被歐洲高估的還有自身的制度吸引力和競爭力,。調(diào)查結果顯示,,一些域外民眾被歐洲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但又拒絕接受歐式的政治說教和道德洗腦,,這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大量移民進入歐洲但歸化認同問題越來越嚴重的現(xiàn)象,。如果解決不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問題,歐洲將陷入吸引力與認同性之間持續(xù)對抗難以和解的惡性循環(huán),。
一旦從反思并批判所謂“民主對抗專制”的二元對抗思維再前進一步,歐洲就更能接受一種不僅需要和中美俄這些大國打交道,,還要和日印加這些“中等強國”促聯(lián)合,,更要和“全球南方”搞合作的復雜局面,而不是偏狹地執(zhí)著于“西方”的身份認同并在小圈子里畫地為牢,。如果能再理性一些,,歐洲應當果斷拋棄“歐洲是花園、世界是叢林”的單一中心觀,,真正嚴肅地去認識俄烏,、巴以等一系列沖突的體系根源,去反思落實經(jīng)濟安全,、推進戰(zhàn)略自主的合理指向,,從而為自己的生存發(fā)展找到更適宜的土壤、培育出更發(fā)達的根系,。
但要在更抽象的層面完全接受國際秩序去中心化,、國際格局多極化的現(xiàn)實,對歐洲民眾甚至精英來說可能要更困難,。畢竟迄今為止大多數(shù)時候,,歐洲仍主要活在自己的歷史經(jīng)驗和世界觀中,對“國強不霸”“共同安全”和“多極依存”等來自其他文明的經(jīng)驗,、具有創(chuàng)新性并最有利于消弭亂局的愿景既不熟悉也不信任,。好在形勢比人強,一旦有了更開闊的眼界和更理性的反應,,歐洲應該能夠認清并順應形勢的變化方向,,并且勇于更新那些不合時宜的世界觀,盡管這個過程對于一向自視為“世界中心”和“精神高地”的歐洲來說很不輕松,。(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區(qū)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相關新聞
美媒:俄烏沖突“改變戰(zhàn)爭樣貌” 無人機成為主角
2024-02-28 11:39:44美媒:俄烏沖突“改變戰(zhàn)爭樣貌”美軍歐洲司令:俄軍已經(jīng)補充了損失 規(guī)模比俄烏沖突爆發(fā)時還大
2024-04-13 17:18:37美軍歐洲司令:俄軍已經(jīng)補充了損失俄防長:西方直接參與俄烏沖突,證據(jù)曝光
2024-04-27 06:50:57俄防長:西方直接參與俄烏沖突俄外交部:北約對俄開展混合戰(zhàn)爭并介入俄烏沖突
當?shù)貢r間5月4日,,俄羅斯外交部發(fā)言人扎哈羅娃表示,,北約和其成員國領導人正在做他們最擅長的事,,也就是造謠和煽動反俄狂熱,以便正當化歐洲規(guī)??涨暗能娛禄?。
2024-05-04 21:46:54俄羅斯外交部專家談伊以局勢及俄烏沖突等問題 援烏迫在眉睫
2024-04-18 06:13:24專家談伊以局勢及俄烏沖突等問題烏學者稱俄新防長人選對烏是壞消息 加劇軍備競賽擔憂
2024-05-13 13:29:16烏學者稱俄新防長人選對烏是壞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