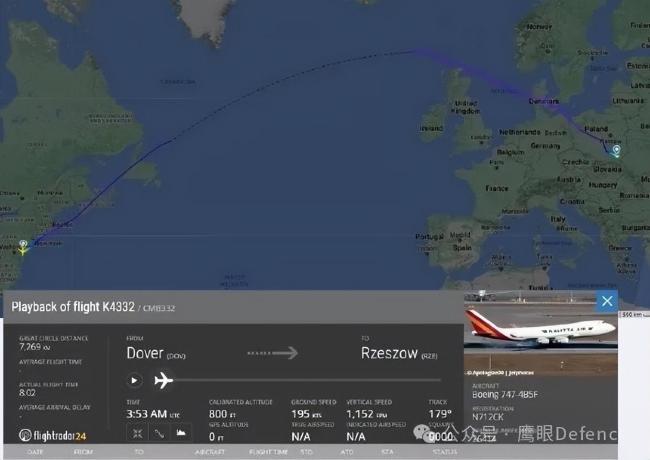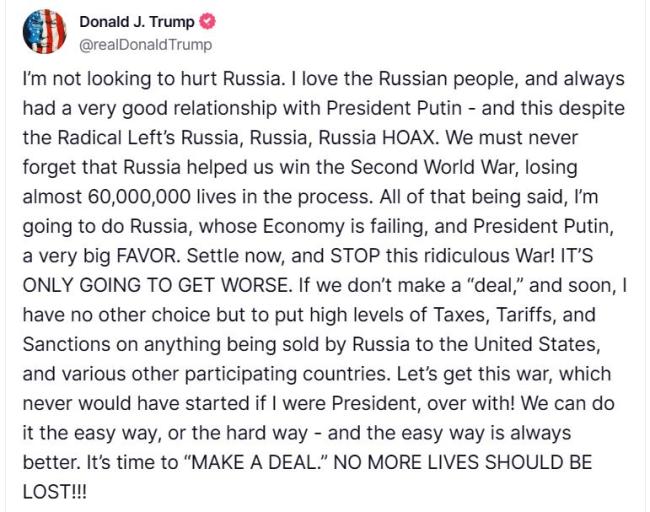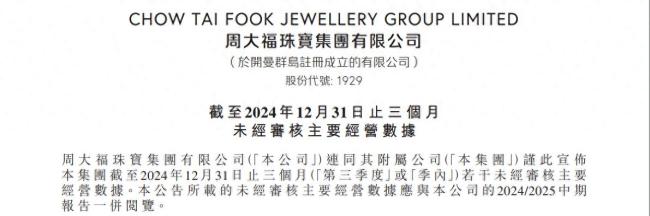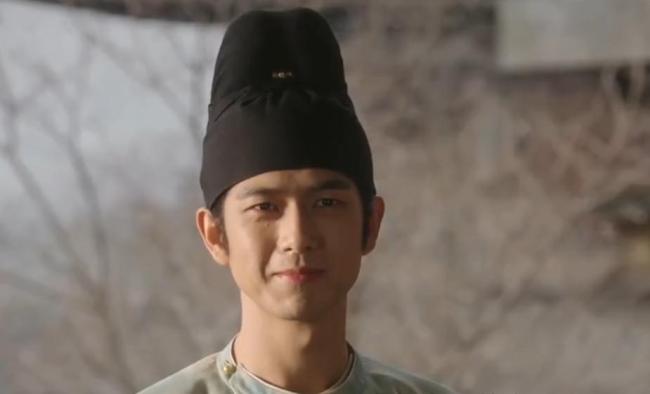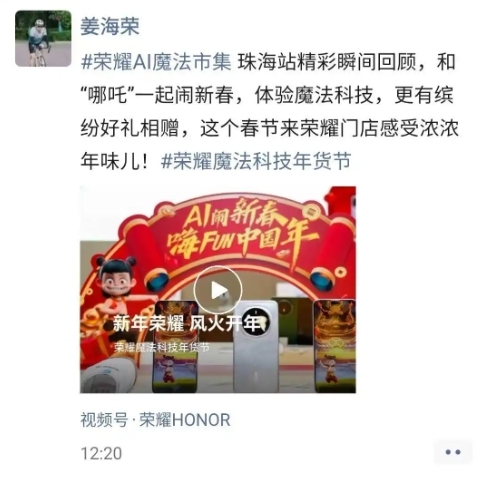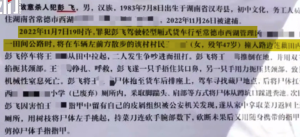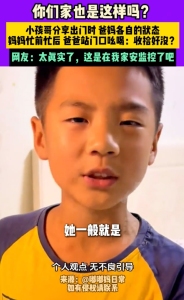13歲少女發(fā)現(xiàn)1億多年前恐龍足跡 意外揭開(kāi)古生物秘密
2006年,,甘肅靖遠(yuǎn)烏蘭鎮(zhèn),,13歲的少女王雪琴在家附近的巖壁上發(fā)現(xiàn)了一些奇怪的印記,。當(dāng)時(shí)她并不知道,,這些印記其實(shí)是近1億年前的恐龍足跡,。
2025年1月6日,甘肅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教授李大慶,、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館員李巖和中國(guó)地質(zhì)大學(xué)(北京)副教授邢立達(dá)等學(xué)者宣布,,在甘肅省靖遠(yuǎn)縣烏蘭鎮(zhèn)發(fā)現(xiàn)了一批距今1.3-1.2億年前的恐龍足跡,被確認(rèn)為白堊紀(jì)斯氏蹺腳龍足跡,。這是迄今甘肅記錄的保存最好的一批獸腳類(lèi)恐龍足跡之一,。這些足跡不僅提供了形態(tài)上的新信息,還在恐龍行為學(xué)方面帶來(lái)了新的成果,,標(biāo)志著烏蘭鎮(zhèn)成為白堊紀(jì)河口群中第五個(gè)足跡富集的地區(qū),。相關(guān)研究成果發(fā)表在學(xué)術(shù)期刊《歷史生物學(xué)》上。
中國(guó)西北的河口群是我國(guó)四足動(dòng)物足跡數(shù)量最豐富,、多樣性最高的白堊紀(jì)地層之一,。學(xué)者們?cè)邴}鍋峽、關(guān)山,、中鋪和紅古四個(gè)地區(qū)陸續(xù)記錄了約31個(gè)下白堊統(tǒng)四足動(dòng)物足跡點(diǎn),,包含超過(guò)一千個(gè)恐龍足跡。這些足跡包括多種三趾型獸腳類(lèi)足跡,,如蹺腳龍足跡,、實(shí)雷龍足跡和亞洲足跡等。
1970年代,,靖遠(yuǎn)烏蘭鎮(zhèn)一個(gè)村落修河堤時(shí),,新暴露了一些白堊紀(jì)的巖層。2006年,,當(dāng)?shù)?3歲少女王雪琴在家附近的巖壁上發(fā)現(xiàn)了奇怪的印記,。2020年,她意識(shí)到這些印記可能是恐龍足跡,,并向當(dāng)?shù)匚奈锞謭?bào)告,。2023年6月,李大慶,、邢立達(dá)等學(xué)者考察了這個(gè)化石點(diǎn)并展開(kāi)了研究,。
烏蘭足跡點(diǎn)位于一處懸崖,懸空在一人高的巖層底部,,面積約6.2平方米,。此次發(fā)現(xiàn)的恐龍足跡都為三趾足跡,至少有67個(gè),,長(zhǎng)度范圍在11厘米至21厘米之間,,沒(méi)有保存第一趾和尾跡,第二趾與第四趾的趾間角較寬等特征,,使其可以歸入中國(guó)侏羅—白堊紀(jì)常見(jiàn)的斯氏蹺腳龍足跡,。留下這些足跡的恐龍臀高約為0.6米至0.9米,,體長(zhǎng)最大可達(dá)2.5米,行走時(shí)幾乎呈直線,。
此次發(fā)現(xiàn)的大小相近的足跡組成了12道行跡,,部分行跡相互平行,行進(jìn)方向相同,。李大慶等學(xué)者用異特龍的復(fù)原三維數(shù)據(jù)模擬后發(fā)現(xiàn),,這些體型相似的獸腳類(lèi)恐龍以步行速度行進(jìn),在前進(jìn)時(shí)形成了一個(gè)相對(duì)密集的陣型,,個(gè)體彼此之間的距離低于身體寬度。這表明這類(lèi)造跡者可能具有群居行為,,這種行為可能是每個(gè)小型造跡者自我防衛(wèi),、防止被天敵捕食的策略之一,它們彼此靠近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減少個(gè)體的警戒壓力,。
此外,,一些足跡保存了橫向拖痕,表明獸腳類(lèi)造跡者曾在行走時(shí)發(fā)生側(cè)滑,,但此后迅速恢復(fù)了平衡,。拖痕由密集的條紋組成,條紋的寬度平均0.7毫米,,間隔約1毫米,,代表了恐龍腳底鱗片的寬度與間隔。這些保存完好的足跡不僅為斯氏蹺腳龍足跡在中國(guó)下白堊統(tǒng)的廣泛分布提供了新的科學(xué)證據(jù),,也為學(xué)者深入了解其足跡形態(tài)和行為學(xué)提供了新的線索,。
相關(guān)新聞
世界上已發(fā)現(xiàn)的最小恐龍足跡化石之一 揭示恐龍小型化演進(jìn)之謎
2024-08-11 12:34:12世界上已發(fā)現(xiàn)的最小恐龍足跡化石之一英國(guó)發(fā)現(xiàn)該國(guó)迄今最大規(guī)模恐龍足跡 揭示侏羅紀(jì)生態(tài)互動(dòng)
2025-01-03 13:04:22英國(guó)發(fā)現(xiàn)該國(guó)迄今最大規(guī)??铸堊阚E你見(jiàn)過(guò)不到3厘米的恐龍足跡化石嗎
2024-08-12 13:17:58你見(jiàn)過(guò)不到3厘米的恐龍足跡化石嗎13歲少女與網(wǎng)友見(jiàn)面遭不法侵害 強(qiáng)制報(bào)告制度顯效
2024-11-28 17:14:5413歲少女與網(wǎng)友見(jiàn)面遭不法侵害恐龍家族再添新丁 內(nèi)蒙古發(fā)現(xiàn)“百年鴛鴦龍”
2024-12-02 13:08:03恐龍家族再添新丁香港首次發(fā)現(xiàn)恐龍化石 專(zhuān)家推測(cè)種類(lèi)與年代
2024-10-24 15:55:05香港首次發(fā)現(xiàn)恐龍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