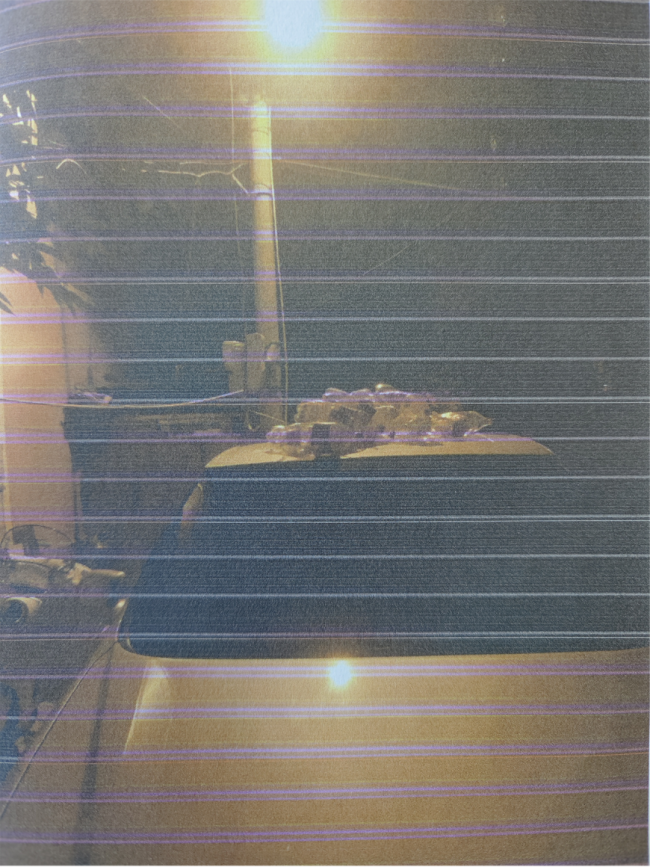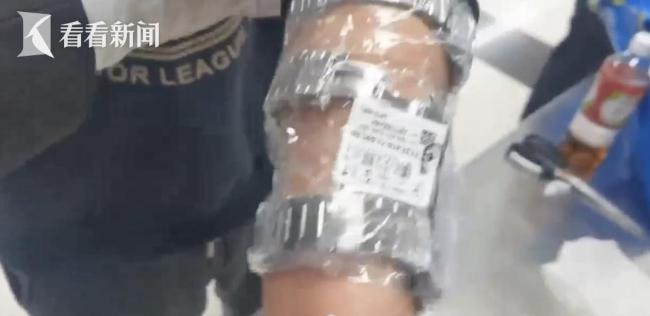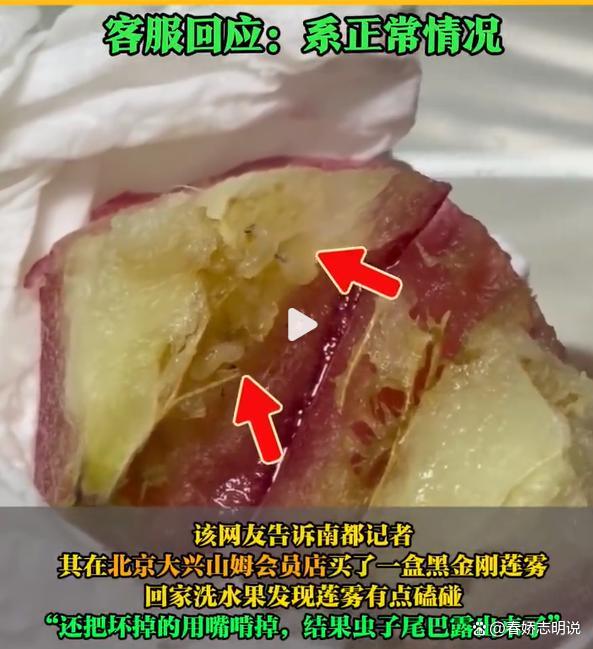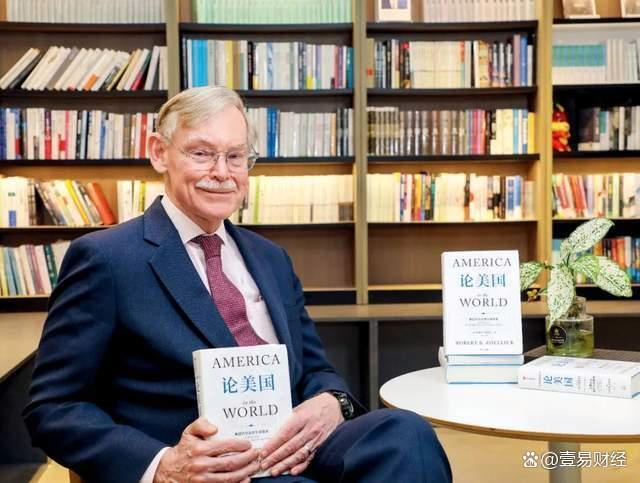代表建議允許科研人員兼職創(chuàng)業(yè) 激發(fā)科研成果轉(zhuǎn)化動力
代表建議允許科研人員兼職創(chuàng)業(yè),!史浩飛指出,,科技創(chuàng)新與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的深度融合是推動經(jīng)濟高質(zhì)量發(fā)展、培育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的關(guān)鍵路徑,,也是建設(shè)科技強國,、保障產(chǎn)業(yè)鏈安全的核心戰(zhàn)略需求。當前,,全球科技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新一代信息技術(sh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領(lǐng)域加速變革,,產(chǎn)業(yè)升級對科技創(chuàng)新的引領(lǐng)性、適配性提出更高要求,。
他認為,,推動科技創(chuàng)新和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深度融合,是落實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xiàn)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重要支撐,。通過融合,可以加速科技成果產(chǎn)業(yè)化,推動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升級,、新興產(chǎn)業(yè)壯大和未來產(chǎn)業(yè)布局,,形成“科技強—產(chǎn)業(yè)強—經(jīng)濟強”的良性循環(huán)。
史浩飛認為,,高校和科研機構(gòu)的科研方向偏重學術(shù)導向,,原創(chuàng)性和前瞻性成果不足,難以滿足產(chǎn)業(yè)對關(guān)鍵技術(shù)的迫切需求,。由于創(chuàng)新鏈與產(chǎn)業(yè)鏈協(xié)同不足,,科研機構(gòu)與企業(yè)缺乏有效對接機制,大量成果滯留在實驗室階段,。此外,,企業(yè)參與科技決策的機制不完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多由高校院所主導,,企業(yè)的“出題人”作用未充分發(fā)揮,。
在成果轉(zhuǎn)化機制方面,史浩飛指出職務(wù)科技成果產(chǎn)權(quán)歸屬模糊,,科研人員轉(zhuǎn)化動力不足,;中試基地、概念驗證平臺等公共支撐平臺建設(shè)滯后,,導致技術(shù)從實驗室到市場的“死亡之谷”難以跨越,。他還提到目前科技金融對早期項目的支持不足,稅收優(yōu)惠和風險補償機制不完善,,導致企業(yè)承擔轉(zhuǎn)化風險的能力弱,。
關(guān)于人才流動與培養(yǎng)體系,史浩飛指出高校與企業(yè)人才“雙開門”機制缺失,,科研人員向產(chǎn)業(yè)界流動的通道不暢,,復合型人才匱乏,既懂技術(shù)又通產(chǎn)業(yè)的高端人才稀缺,。高?!捌莆逦ā备母锫鋵嵅坏轿唬己梭w系仍以論文,、課題為主,,忽視產(chǎn)業(yè)實踐貢獻。
針對上述問題,,史浩飛建議強化企業(yè)創(chuàng)新主體地位,構(gòu)建協(xié)同攻關(guān)機制,。在國家重大科技專項中明確企業(yè)牽頭責任,,支持領(lǐng)軍企業(yè)聯(lián)合中小企業(yè)、高校組建創(chuàng)新聯(lián)合體,建立“企業(yè)出題,、科研答題,、市場閱卷”的閉環(huán)機制。同時,,完善企業(yè)研發(fā)費用加計扣除,、稅收優(yōu)惠等政策,鼓勵企業(yè)加大未來產(chǎn)業(yè)技術(shù)布局投入,。
他還提議進一步完善成果轉(zhuǎn)化全鏈條支撐體系,,建立職務(wù)科技成果單列管理制度,明確所有權(quán),、收益權(quán)分配規(guī)則,,激發(fā)科研人員轉(zhuǎn)化動力。加快建設(shè)國家級中試基地,、概念驗證中心,,提供技術(shù)評估、商業(yè)化驗證等公共服務(wù),,并發(fā)展“耐心資本”和科技保險,,覆蓋轉(zhuǎn)化早期高風險環(huán)節(jié)。
在人才流動機制方面,,史浩飛建議暢通人才雙向流動,,培養(yǎng)復合型創(chuàng)新人才。推動高校與企業(yè)共建“人才旋轉(zhuǎn)門”機制,,允許科研人員兼職創(chuàng)業(yè)并保留職稱待遇,;優(yōu)化“破五唯”評價體系,將成果轉(zhuǎn)化貢獻納入考核,。實施跨界人才培養(yǎng)計劃,,依托產(chǎn)教融合平臺聯(lián)合培養(yǎng)“科學家+工程師”復合型團隊。
相關(guān)新聞
建議允許食用野豬 解決種群調(diào)控難題
2024-11-04 09:33:00建議允許食用野豬代表:建議醫(yī)院檢查結(jié)果實行共享互認
2025-03-06 13:56:20建議醫(yī)院檢查結(jié)果實行共享互認代表委員的建議提案到底有沒有用 實際成效顯著
2025-03-06 15:11:46代表委員的建議提案到底有沒有用代表建議將元宵節(jié)設(shè)為法定節(jié)假日 致敬傳統(tǒng)文化
2025-02-28 17:00:02代表建議將元宵節(jié)設(shè)為法定節(jié)假日代表建議規(guī)范幼師編制 提高教師隊伍穩(wěn)定性
2025-03-08 08:26:23代表建議規(guī)范幼師編制代表建議優(yōu)化農(nóng)村醫(yī)保繳納 減輕農(nóng)民負擔
2025-03-09 17:36:00代表建議優(yōu)化農(nóng)村醫(yī)保繳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