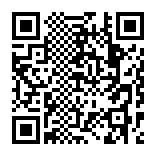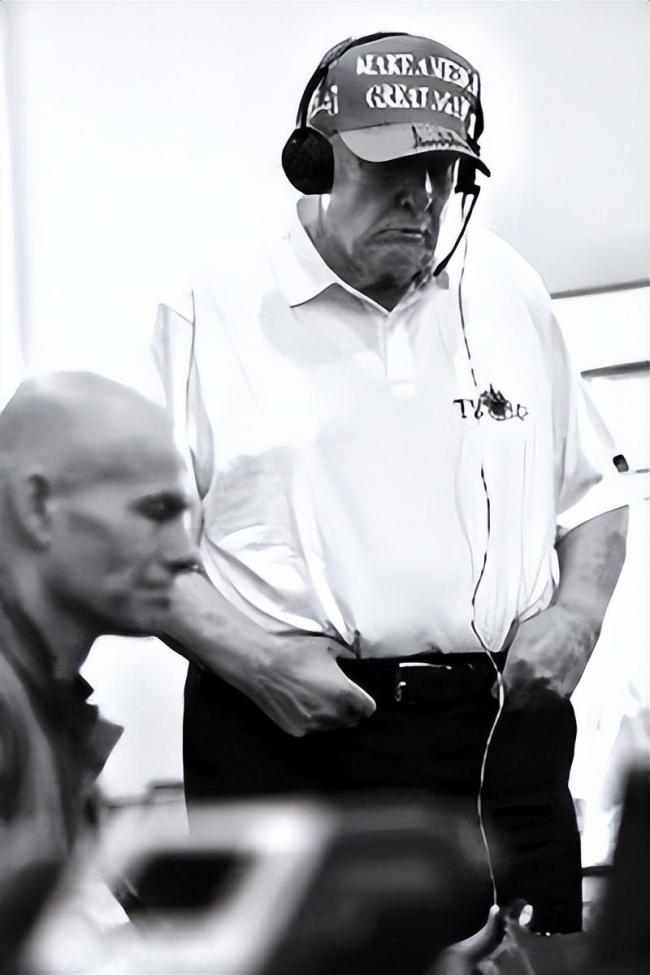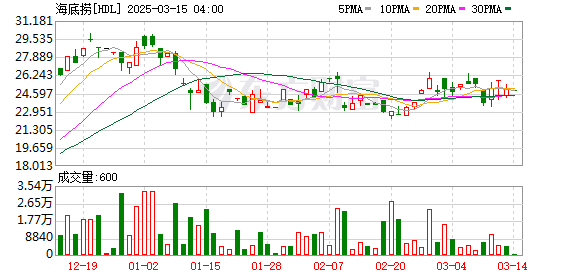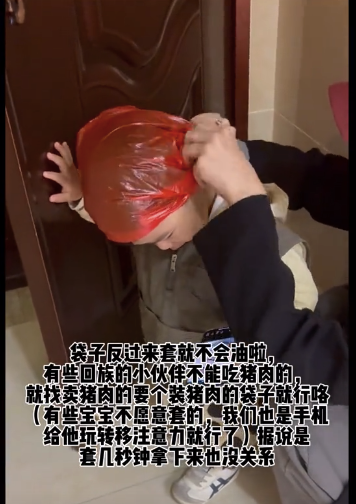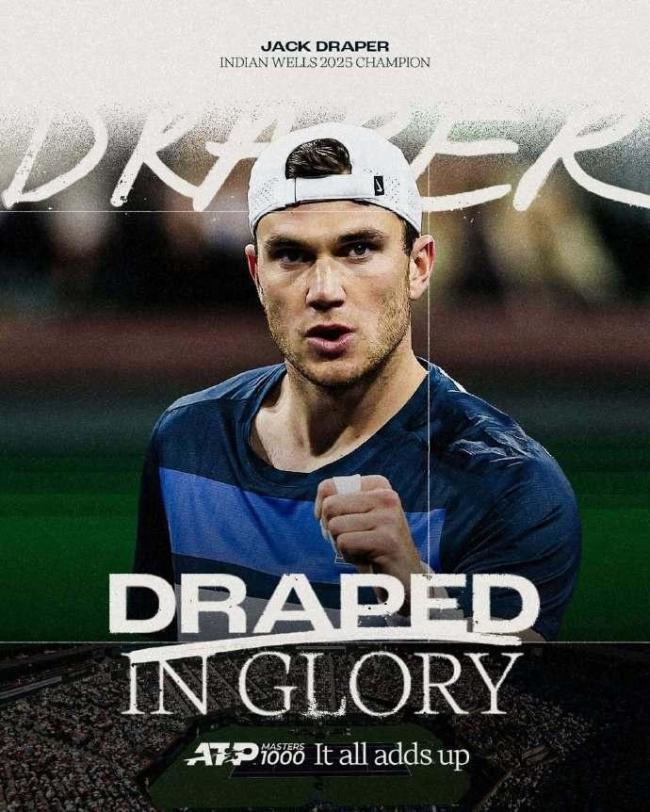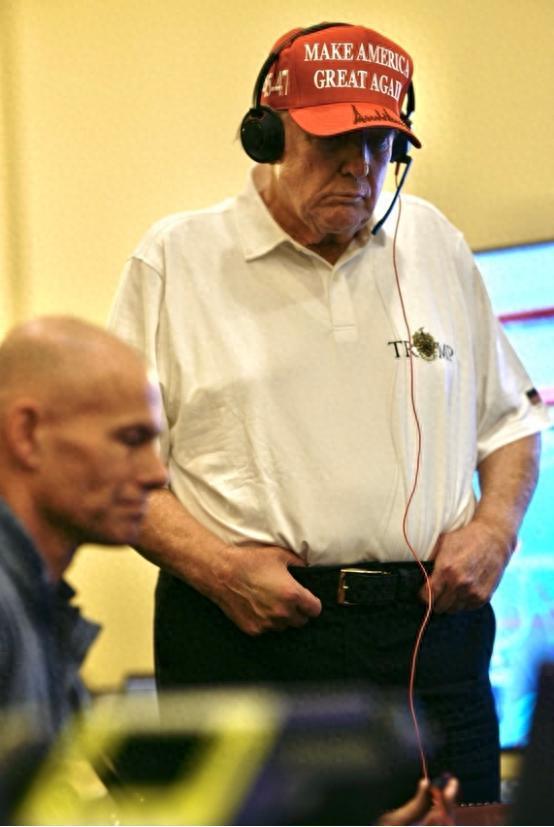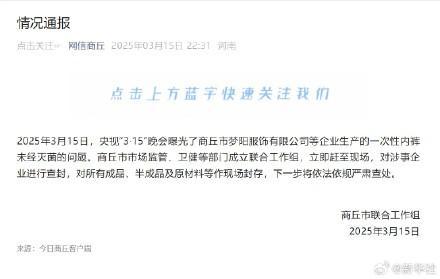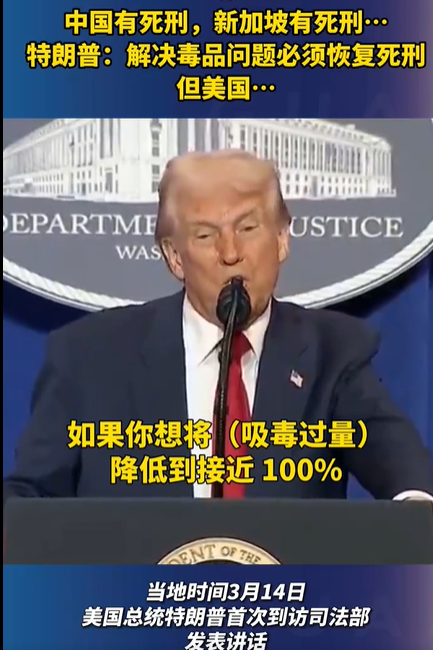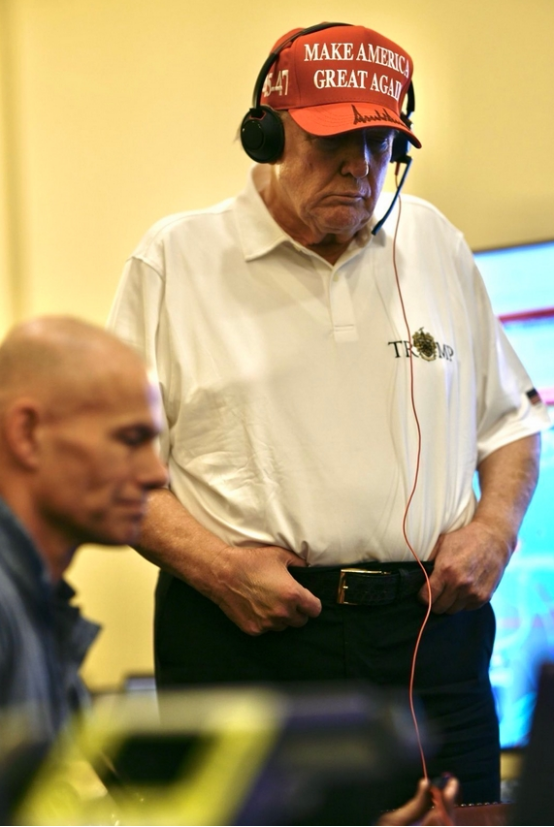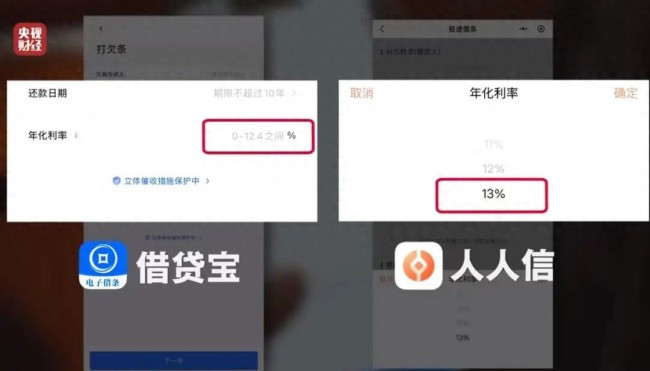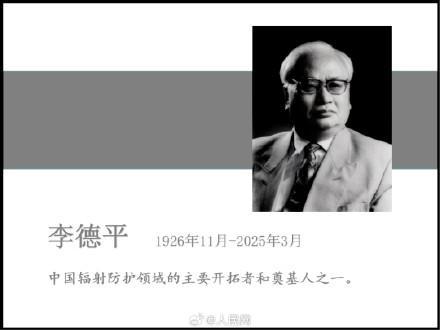德國(guó)大選:一場(chǎng)幾無(wú)懸念的權(quán)力更迭 默茨時(shí)代來(lái)臨(2)
極右翼的德國(guó)選擇黨(AfD)以20.8%的得票率躍居第二大黨,,較2021年增長(zhǎng)逾10個(gè)百分點(diǎn),成為此次選舉最刺眼的“黑馬”,。這一結(jié)果既折射出德國(guó)社會(huì)的深層裂痕,,也為未來(lái)政治穩(wěn)定埋下隱患。選擇黨的崛起源于多重社會(huì)焦慮,。東部地區(qū)對(duì)其支持率高達(dá)34%(西部為18%),,反映出東西德經(jīng)濟(jì)鴻溝的持續(xù)發(fā)酵,;移民問(wèn)題(尤其是2023年難民申請(qǐng)量創(chuàng)八年新高)則成為其煽動(dòng)排外情緒的核心抓手。此外,,中低收入群體對(duì)通脹和生活成本的不滿,,使選擇黨“反全球化”“反精英”的民粹口號(hào)獲得廣泛共鳴。
主流政黨對(duì)選擇黨的聯(lián)合禁令短期內(nèi)難以打破,。默茨明確表示“絕不與選擇黨合作”,,歐盟層面亦將其定性為“反民主力量”。但若經(jīng)濟(jì)困境持續(xù),,選擇黨作為議會(huì)最大反對(duì)黨,,或通過(guò)議題綁架倒逼政策右轉(zhuǎn),,進(jìn)一步?jīng)_擊德國(guó)政治傳統(tǒng),。
盡管默茨宣稱“優(yōu)先尋求理念相近的伙伴”,但實(shí)際選擇極為有限,。聯(lián)盟黨與社民黨合計(jì)得票率45%,,距離過(guò)半仍差約5個(gè)百分點(diǎn)。若兩黨拉攏綠黨(11.6%)組成“黑紅綠聯(lián)盟”(俗稱“肯尼亞聯(lián)盟”),,三黨合計(jì)56.6%的席位可確保穩(wěn)定多數(shù),。這一組合雖非默茨首選,但具有現(xiàn)實(shí)可行性,。默茨稱他期待能在今年復(fù)活節(jié)前完成政府組建,。
即便成功組閣,默茨時(shí)代的德國(guó)仍將面臨內(nèi)外交困的復(fù)雜局面,。經(jīng)濟(jì)復(fù)蘇步履維艱,,德國(guó)2023年GDP萎縮0.3%,工業(yè)訂單連續(xù)18個(gè)月下滑,,能源密集型產(chǎn)業(yè)外流加劇,。默茨承諾的“減稅、去官僚化,、投資基建”能否激活經(jīng)濟(jì)存疑,,而社民黨對(duì)增稅和福利擴(kuò)張的訴求可能削弱改革力度。同時(shí),,歐洲領(lǐng)導(dǎo)權(quán)爭(zhēng)奪白熱化,,默茨主張“歐洲戰(zhàn)略自主”,試圖減少對(duì)美依賴,,但法德在防務(wù),、財(cái)政規(guī)則等議題上的分歧可能加劇。選擇黨的疑歐傾向也將掣肘德國(guó)在歐盟的決策空間,。
德國(guó)大選結(jié)果看似“無(wú)懸念”,,卻暗藏政治重構(gòu)的驚雷,。默茨的組閣權(quán)雖無(wú)懸念,但其能否帶領(lǐng)德國(guó)走出困境,、遏制極右翼蔓延,、重塑歐洲影響力,仍需時(shí)間檢驗(yàn),。這場(chǎng)選舉不僅是權(quán)力的更迭,,更是一場(chǎng)關(guān)于德國(guó)方向的選擇——在保守與變革、開放與封閉,、歐洲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撕裂中,,這個(gè)歐洲引擎的每一次轉(zhuǎn)向都將牽動(dòng)世界的神經(jīng)。
相關(guān)新聞
德國(guó)執(zhí)政聯(lián)盟破裂 或面臨提前大選
2024-11-07 11:35:42德國(guó)大選或提前舉行默茨點(diǎn)名馬斯克干涉德國(guó)大選
2025-02-25 11:18:26默茨點(diǎn)名馬斯克干涉德國(guó)大選德國(guó)大選不再“無(wú)聊”,歐洲人卻開始擔(dān)心
2025-02-20 13:49:09德國(guó)大選不再“無(wú)聊”默茨宣布獲勝 一場(chǎng)大選改變德國(guó)政局 德國(guó)政局迎來(lái)新變局
2025-02-24 07:47:31默茨宣布獲勝一場(chǎng)大選改變德國(guó)政局德國(guó)大選后綠黨能否延續(xù)造王者角色
2025-02-21 10:51:36德國(guó)大選后綠黨能否延續(xù)造王者角色德國(guó)大選前夕又現(xiàn)襲擊事件 安全憂慮加劇
2025-02-14 11:51:43德國(guó)大選前夕又現(xiàn)襲擊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