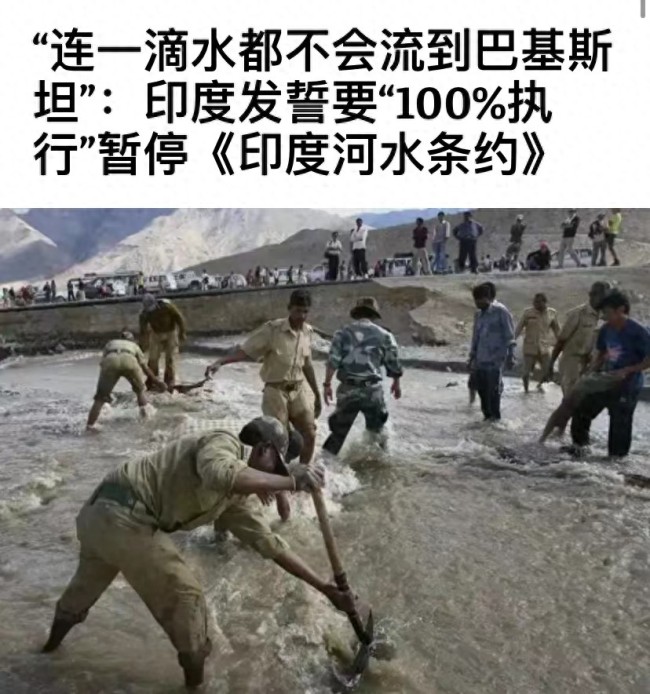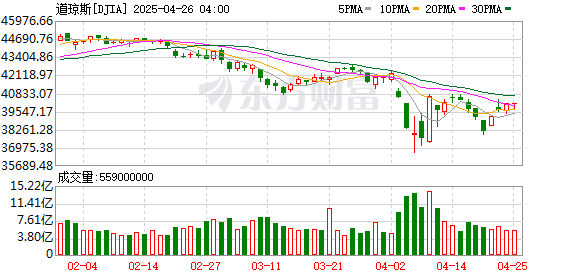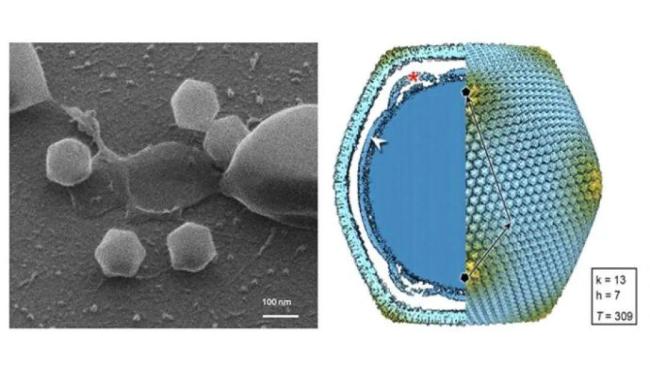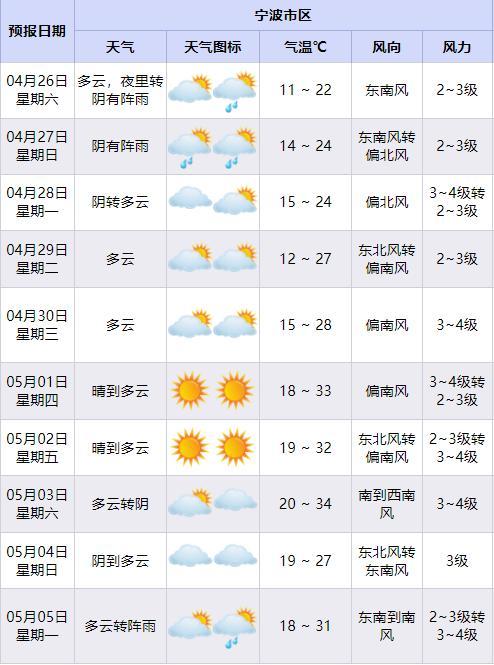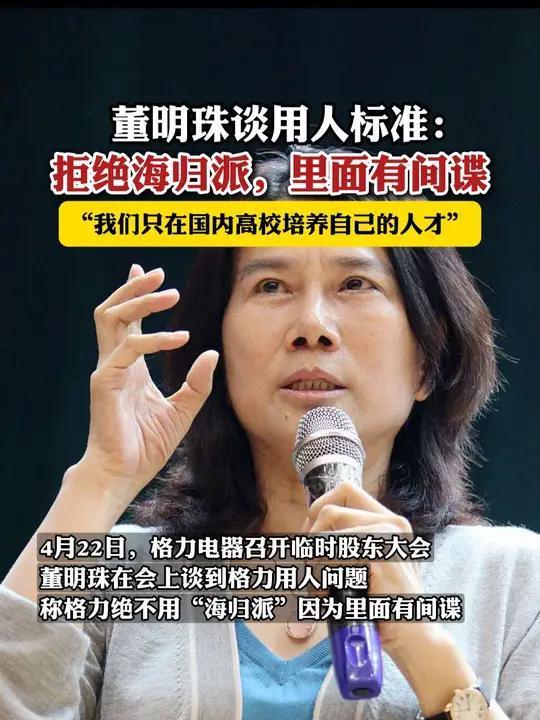醫(yī)生見(jiàn)過(guò)最好的死亡告別,!只有思考過(guò)死亡,,才能更好地活著(2)
60多歲中風(fēng),,79歲心臟停博,但很幸運(yùn)地有驚無(wú)險(xiǎn),。他到82歲才退休,,停止工作的原因,是因?yàn)槠拮迂惱枰疹櫋?/p>
貝拉因病失明,,并伴隨嚴(yán)重的記憶力衰退,。菲力克斯給貝拉做飯,帶她散步,,看醫(yī)生,,他說(shuō):“現(xiàn)在,她就是我的目標(biāo),?!?/p>
照顧妻子的同時(shí),菲力克斯客觀地記錄自己身體的變化:皮膚干燥,、嗅覺(jué)退化,、夜間視力變差、容易疲勞,、開(kāi)始掉牙。
但是他采取了所有能采取的措施,,比如每周騎3次健身腳踏車,,每年看兩次牙醫(yī)等等,讓衰老的曲線盡量平緩,,而不是“飛流直下”,。
他知道,如果不能誠(chéng)實(shí)地面對(duì)自己的局限性,,那么就無(wú)法幫助到妻子,。
把常規(guī)體檢納入生活、為未來(lái)未雨綢繆,,并做出必要的改變來(lái)減緩身體機(jī)能的衰退,,會(huì)讓老年生活更有質(zhì)量。
適應(yīng)變化很難,,但學(xué)會(huì)接受現(xiàn)實(shí)更有必要,。
王蒙曾說(shuō):“衰老是肯定的,這不由我拍板,何時(shí)衰老,,同樣不聽(tīng)誰(shuí)的批示:這是多么快樂(lè),,明年我將衰老,這是多么平和,,今天仍然活著,。”
不必畏懼衰老,,我們要學(xué)會(huì)的是,,在觀念上做準(zhǔn)備,在實(shí)踐中學(xué)適應(yīng),。
保持健康,,也要滋養(yǎng)心靈
把照顧妻子作為目標(biāo),成為菲力克斯自我價(jià)值的來(lái)源,。
每個(gè)生命都是如此,,對(duì)生活的要求也不僅僅簡(jiǎn)化到健康和安全,更需要心靈支撐,。
每位老年人,,都需要足夠的心理疏解與心靈撫慰,而不僅僅是生活的照顧,。
很多老年人畏懼去養(yǎng)老院,,他們懼怕的,不是我們想象的缺乏親人陪伴或者照顧不周,,而是養(yǎng)老院的“三大瘟疫”:倦怠感,、孤獨(dú)感、無(wú)助感,。
不論醫(yī)院,,還是大多數(shù)療養(yǎng)院,甚至子女,,對(duì)此都很少有積極的思考和措施:
在我們衰老脆弱時(shí),,如何使生活存在價(jià)值?
相關(guān)新聞
德拉普:凱恩是我見(jiàn)過(guò)最好的球員 難以置信的體驗(yàn)
2025-03-22 15:42:57德拉普保羅:這是我見(jiàn)過(guò)文班打得最好的一場(chǎng) 家鄉(xiāng)表現(xiàn)驚艷眾人
2025-01-25 12:14:59保羅戒煙的驚人效果,!醫(yī)生:最好的戒煙時(shí)間就是現(xiàn)在
2025-03-27 10:21:39醫(yī)生:最好的戒煙時(shí)間就是現(xiàn)在摩根:C羅說(shuō)梅西是他見(jiàn)過(guò)最好的球員,,但隨后笑稱他不看自己踢球 昔日專訪再被提及
2025-02-06 14:17:42摩根醫(yī)生給失眠女友打麻醉藥致其死亡
為了緩解女友的失眠癥狀,,四川一醫(yī)院麻醉科醫(yī)生瞿某在酒店里,先后分20多次將1300毫克丙泊酚(短效靜脈麻醉藥),,通過(guò)腳踝注射方式注射進(jìn)女友體內(nèi),。
2024-11-13 09:43:38醫(yī)生給失眠女友打麻醉藥致其死亡這樣的西藏你見(jiàn)過(guò)嗎?
2025-03-29 08:06:00這樣的西藏你見(jiàn)過(gu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