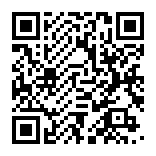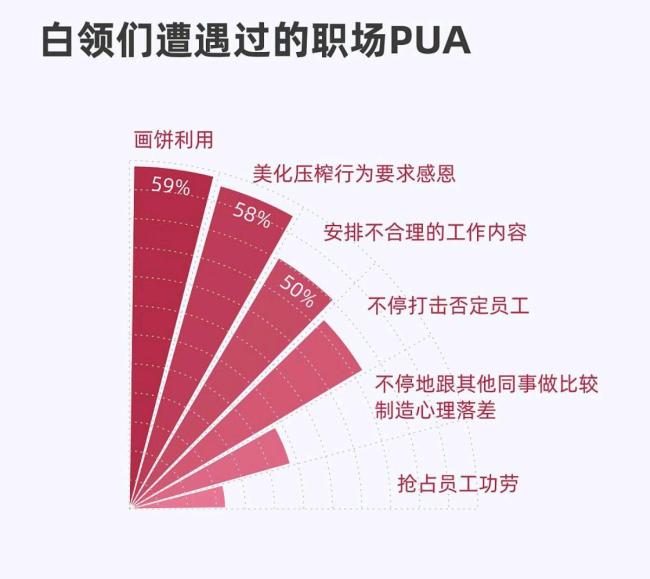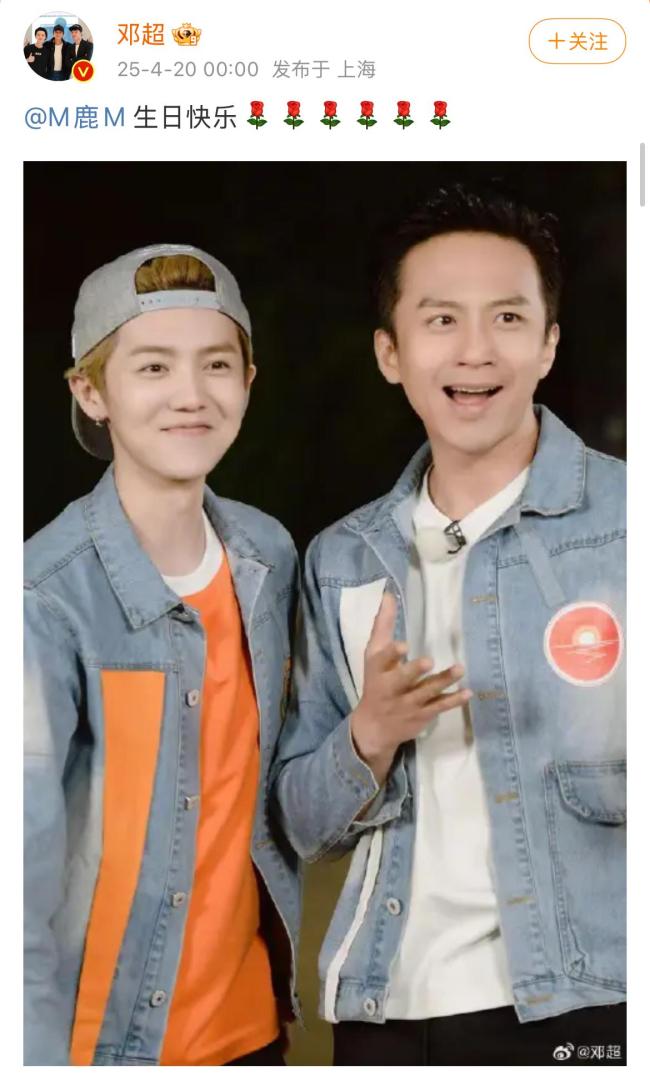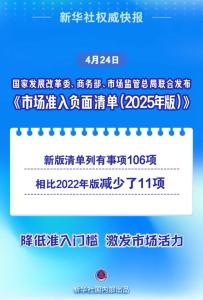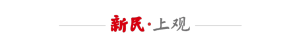大V:特朗普低估俄烏局勢復(fù)雜程度 單邊行動(dòng)難奏效(2)

特朗普的商業(yè)背景塑造了其獨(dú)特的“交易藝術(shù)”外交風(fēng)格,,核心特征是短期利益最大化、談判姿態(tài)不可預(yù)測性以及協(xié)議本身的媒體曝光度優(yōu)先,。這種風(fēng)格在處理朝核問題等雙邊博弈中或許具有戰(zhàn)術(shù)價(jià)值,,但在涉及多邊利益、歷史積怨與領(lǐng)土主權(quán)的俄烏沖突中卻適得其反,。特朗普要求烏克蘭政府“展現(xiàn)靈活性”的表態(tài),,本質(zhì)上是用房地產(chǎn)談判思維解構(gòu)地緣政治矛盾。當(dāng)國務(wù)卿盧比奧設(shè)定“48小時(shí)評估期限”時(shí),,這種做法既忽視了俄羅斯對戰(zhàn)略緩沖區(qū)的剛性需求,,也低估了烏克蘭維護(hù)領(lǐng)土完整的民族意志。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對“高調(diào)撤出”策略的偏愛(如退出《巴黎協(xié)定》《伊朗核協(xié)議》),,使得沖突雙方始終懷疑美國承諾的可持續(xù)性。
自2017年“美國優(yōu)先”原則確立以來,,特朗普政府逐步解構(gòu)了二戰(zhàn)后美國主導(dǎo)的自由國際主義秩序,。這種價(jià)值觀轉(zhuǎn)向在俄烏沖突中表現(xiàn)為三重矛盾:對人權(quán)話語的選擇性使用削弱了支持烏克蘭的道德正當(dāng)性;對歐洲能源自主權(quán)的干預(yù)(阻撓北溪2號項(xiàng)目)暴露出利益至上的實(shí)用主義,;對國際法的工具化態(tài)度使得美國難以在頓巴斯地位問題上建立公正仲裁者形象。當(dāng)盧比奧強(qiáng)調(diào)“重新分配戰(zhàn)略資源”時(shí),,實(shí)質(zhì)是將烏克蘭危機(jī)置于大國競爭框架下考量,,這種價(jià)值觀的功利主義轉(zhuǎn)向,使得美國既無法獲得全球南方國家的道義支持,,也難以維系西方陣營的內(nèi)部團(tuán)結(jié),。
美國調(diào)解能力的弱化與其綜合實(shí)力相對下滑密切相關(guān)。經(jīng)濟(jì)層面,,截至2024財(cái)年,,聯(lián)邦政府債務(wù)/GDP突破120%,制約了對烏長期援助能力,;軍事層面,,海軍艦艇數(shù)量降至冷戰(zhàn)以來最低水平,,難以同時(shí)在印太與歐洲維持戰(zhàn)略威懾;軟實(shí)力方面,,皮尤研究中心數(shù)據(jù)顯示,,美國國際形象在57個(gè)國家中的認(rèn)可度較2016年下降12個(gè)百分點(diǎn)。這種實(shí)力變遷導(dǎo)致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采取“成本外化”策略:通過施壓歐洲增加防務(wù)開支,、推動(dòng)烏克蘭接受領(lǐng)土讓步來降低美國投入,。然而俄羅斯在能源武器化與核威懾升級方面的反制,使得美國的“極限施壓”手段難以奏效,。
相關(guān)新聞
大V:俄軍在庫爾斯克勢如破竹
2025-03-13 10:18:33俄軍在庫爾斯克勢如破竹大V:牛市大概率并未結(jié)束,慢牛行情可期,?
2024-10-10 14:53:41大V:牛市大概率并未結(jié)束大V:能立竿見影提振信心的唯有股市
2024-10-18 15:05:41大V:能立竿見影提振信心的唯有股市大V:李在明若上臺(tái)必有大動(dòng)作 中韓關(guān)系走向成謎
2025-04-05 22:47:03大V網(wǎng)絡(luò)“大V”司馬南偷稅被罰超900萬
2025-03-21 10:21:39網(wǎng)絡(luò)“大V”司馬南偷稅被罰超900萬大V:以色列不信任敘利亞新政權(quán) 質(zhì)疑風(fēng)暴再起
2025-01-01 16:16:16以色列不信任敘利亞新政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