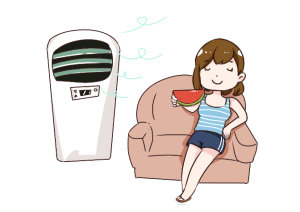塞罕壩夫妻瞭望員:兒子曾說“林子才是兒子”(4)
這些年,,兒子劉志剛“殘缺”的少年時代成了劉軍,、齊淑艷夫妻最大的遺憾。
劉志剛從小學開始就在圍場縣城的一家寄宿制私立學校上學,,幾個月才能回家一次,,都是自己乘坐塞罕壩機械林場至圍場縣城的長途客車,為了不讓兒子在外受欺負,,劉軍夫婦每次都要給他充足的錢,,讓他去與同學“交往”。
然而,,劉志剛在學校并不受同學待見,,還經(jīng)常會被稱為沒有爸爸媽媽的“野孩子”,。
“因為這個事,兒子在學校經(jīng)常打架,,那時候他不理解父母的工作性質,,回家的時候還跟我們說不是我們的兒子,那片林子才是我們的兒子,?!饼R淑艷說。
上初中的時候,,劉志剛體會到了父母的艱辛,,在放假的時候主動回到林場幫父母干活,學著瞭望,。有時也會帶著同學到他“家”住上幾天,,跟同學們聊著這片讓他“受傷”的林子。
劉志剛中專畢業(yè)后去了上海一家公司工作,,月薪7千多,,他還做了幾份兼職,一個月下來加一起能夠掙到1萬多,,但劉軍夫婦害怕兒子在外“遭難”,,還堅持要把兩人的7千多工資寄給兒子。
“看著兒子在外工作很辛苦,,想想還不如家里,,就在塞罕壩幫著他先物色了個崗位,雖說掙得不多,,但心里踏實,,兒子能夠在身邊,我們能夠多陪陪他,?!眲④姺Q,,現(xiàn)在的年輕人沒人愿意再干瞭望員這個職業(yè)了,,他們寧可不干也不會上山來。

齊淑艷在記錄值班日志,。
理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后,,劉志剛辭去上海的工作,回到塞罕壩林場后被暫時安置在了陰河林場的撲火隊,,成了一名臨時撲火隊員,。
“他回來后我就跟他溝通了讓他接班的想法,他同意了,,現(xiàn)在就是希望他盡快能夠轉正,?!眲④姼嬖V澎湃新聞。
不忙的時候,,劉志剛總是回到“望海樓”幫著父母瞭望,。
今年6月份,劉志剛結婚了,,媳婦是林場附近一家包工頭的女兒,。兒媳也非常支持劉軍夫婦的想法,等他們退休了,,劉志剛夫婦會繼續(xù)留在“望海樓”,,繼續(xù)看護著那片林子。
“兒子回來后,,我們都特別高興,,我一天見不到他都想,每天晚上要微信視頻,,聊聊家常,。”齊淑艷說,。
相關新聞
北京世園會河北園——綠染太行 淀泊風光
河北園中的雄安新區(qū)標志。本報記者 賀 勇攝 太行山特有的柏坡黃石做成的山形大門,,配以大型雪浪石,,體現(xiàn)出自然山形的流線變化,,兩邊再搭配油松等特色植物,彰顯出濃郁的太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