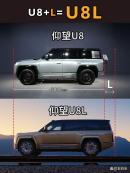疫情之下,用詩歌表達態(tài)度,、記錄洗禮(2)
孫曉婭:苦難中捍衛(wèi)個體生命
詩歌,,作為語言的最高藝術,,在苦難面前,從未缺席,。置身苦難中,,寫作語境與寫作限度不斷發(fā)生變動,詩人們拿起手中的筆,,記錄,、感懷、期冀,、諷喻,,抗爭、警惕,、批判……自古及今,,在苦難中生成的優(yōu)秀的詩歌作品從來不是同一的面孔。
布羅茨基曾言:“文學的功績之一,,在于,,它有助于使我們生存的時間更加個性化?!蹦切┝鱾鞑凰サ慕?jīng)典詩作都藉由苦難表達岀創(chuàng)作主體的精神高度,、思想力量和人格魅力。
上世紀40年代初,,戴望舒被保釋出獄后,,以獄中生活為題材,寫下《等待》《心愿》等詩篇,,其中最感人深摯的是《我用殘損的手掌》,。詩人用屬于心靈的“無形的手掌”,在想象中撫摸祖國的版圖,,戰(zhàn)爭所帶來的殘酷景象與記憶中祖國秀麗壯美的山河,,都在詩人的筆端與腦海一一展開。
他所“摸索”到的首先是戰(zhàn)火中的中國現(xiàn)實,,是被戰(zhàn)爭所摧毀的土地,,沾滿了“血和灰”的深重的苦難,而后是風景如畫的家鄉(xiāng)與祖國的山川自然,,對于記憶中景象的書寫,,反襯著現(xiàn)實的沉重與艱險,,以及詩人對處于災難中的人民的關切。但是,,戴望舒并沒有簡單停留在對于現(xiàn)實苦難的描摹,、勾勒之中,而是充滿激情地表達了個體的期望,?!拔矣脷垞p的手掌”一句,既表明詩人在國家危難之時個人命運遭際的悲苦,,又成為詩人感受災難深重的祖國的方式,,使個體的“殘損”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
托爾斯泰曾言:詩是人們心里燃起來的火,。這種火焰燃燒著,發(fā)出熱,,發(fā)出光,。詩人是身不由己懷揣著“痛苦去燃燒自己并點燃別人的人”,他們捍衛(wèi)的是個體的也是人類的生命書寫,。
相關新聞
戰(zhàn)疫情,,穩(wěn)經(jīng)濟!各地正在全力以“復”,!
央視網(wǎng)消息 (焦點訪談):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給經(jīng)濟社會造成的沖擊,,當前,就是要在一手抓疫情防控的同時,,還要一手抓分區(qū)分級精準復工復產(chǎn)
黨建引領群防群控戰(zhàn)疫情
原標題:楊凌:黨建引領群防群控戰(zhàn)疫情楊凌實現(xiàn)社區(qū)防疫工作黨組織全覆蓋。本報記者程剛攝庚子年伊始,,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斗”在全省上下打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