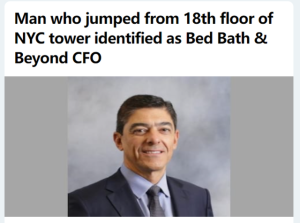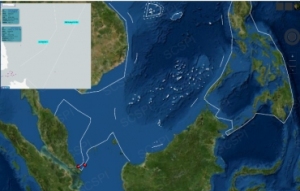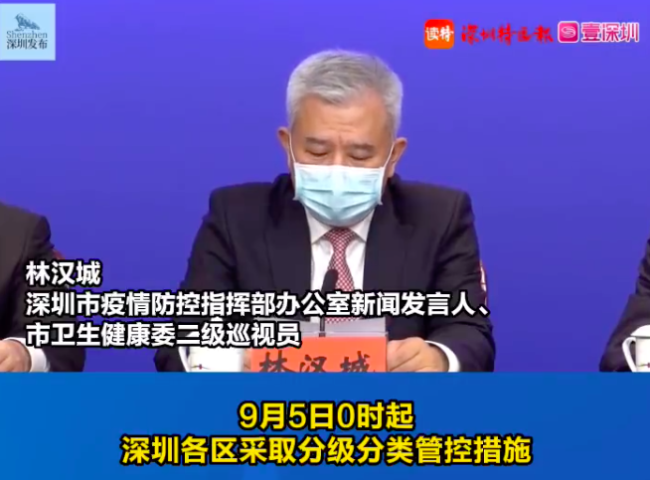黑話,,只是神似高貴罷了:阿爾多諾論海德格爾(2)
黑話對(duì)物化的不斷斥責(zé),本身就是物化的,。它落入了理查·瓦格納在反對(duì)壞藝術(shù)時(shí)所定義的“戲劇效果”的窠臼:沒(méi)有行動(dòng)者的行動(dòng)所帶來(lái)的結(jié)果,。當(dāng)圣靈遠(yuǎn)去,,人們說(shuō)著機(jī)械的話語(yǔ)。他們所暗示的秘密,,從一開(kāi)始就不存在的秘密,,是公開(kāi)的秘密。沒(méi)有秘密的人需要的僅僅是說(shuō),,仿佛他知道這個(gè)秘密而其他人不知道它,。表現(xiàn)主義的格言“每個(gè)人都被選中”(出自被納粹殺害了的保羅·科恩菲爾德的一部戲劇作品)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錯(cuò)誤撤退之后塵,僅僅有助于被社會(huì)發(fā)展所威脅和侮辱的小資產(chǎn)階級(jí)獲得意識(shí)形態(tài)上的虛假滿足,。
黑話在精神中和現(xiàn)實(shí)中都沒(méi)有任何發(fā)展,,這個(gè)事實(shí)是它的賜福——亦即源始性——之源,。尼采活得不夠久,,沒(méi)機(jī)會(huì)對(duì)本真性的黑話感到反胃:在20世紀(jì)的德國(guó),尼采變成了最典型的怨恨現(xiàn)象,。尼采的話“臭不可聞”,,將在幸福生活的洗浴節(jié)中找到用武之地:
“星期天真的是從星期六晚上開(kāi)始的。當(dāng)手工藝者整理好他的工作室,,當(dāng)家庭主婦把屋子收拾得干凈明亮,,連大門前的街道也掃得一塵不染,當(dāng)孩子們也洗好了澡,,成年人便洗去了一周的塵垢,,徹底擦干凈自身,然后穿上準(zhǔn)備好的新衣服:當(dāng)這一切就緒,,帶著一種鄉(xiāng)村的周到與細(xì)心,,于是人產(chǎn)生了一種極為溫暖的休憩感覺(jué)?!?/p>

在書房中的阿多爾諾。
來(lái)自不復(fù)存在的日常生活的那些表達(dá)和情景一直在自吹自擂,,似乎它們被某種絕對(duì)性賦予了權(quán)力和擔(dān)保,,而那絕對(duì)性卻天威難測(cè),。盡管見(jiàn)多識(shí)廣的人總是對(duì)召喚救贖這件事猶豫不決,然而沉迷權(quán)威的人卻安排好了詞語(yǔ)的升天,,以超越現(xiàn)實(shí)的,、有條件的、有爭(zhēng)議的領(lǐng)域—他們甚至在印刷文字中也講著這些詞語(yǔ),,仿佛上蒼的保佑已經(jīng)直接跟著那個(gè)詞來(lái)臨,。“上蒼”,,有待思考的,,卻又對(duì)立于思想的上蒼被黑話損壞了:黑話表現(xiàn)得似乎它“向來(lái)”(用它愛(ài)說(shuō)的話說(shuō))就占有著上蒼。
哲學(xué)想要的個(gè)性——它使得描述成為哲學(xué)不可或缺的東西——決定了哲學(xué)的全部詞語(yǔ)所說(shuō)的要多于每一個(gè)詞語(yǔ),。這一特征被黑話利用了,。真理對(duì)個(gè)別詞語(yǔ)和命題陳述之意義的“超越”被黑話歸屬于各個(gè)詞語(yǔ)本身,似乎詞語(yǔ)占有了這種不可改變的超越性,,而實(shí)際上這種“言外之意”只是通過(guò)星叢的中介才得以形成,。
按照哲學(xué)語(yǔ)言自身的理念,哲學(xué)語(yǔ)言通過(guò)它所說(shuō)的東西在思想鏈條中的發(fā)展而超越了它所說(shuō)的東西,。哲學(xué)語(yǔ)言的辯證超越在于真理和思想之間的矛盾意識(shí)到了自身,,并克服了自身。黑話毀滅性地接管了這一超越性,,把它移交給了黑話自身的“啪嗒啪嗒”,。這里,詞語(yǔ)的任何言外之意,、話外之音都被一勞永逸地搞成了表達(dá),。辯證法中斷了:詞與物之間的辯證法中斷了,語(yǔ)言內(nèi)部的辯證法——個(gè)別詞語(yǔ)與其關(guān)系之間的辯證法——也中斷了,。詞語(yǔ)不再被判斷,,不再被思考,而是將其意義拋在腦后,。
這樣一來(lái),,上述“言外之意”的現(xiàn)實(shí)就被建構(gòu)好了;而這就是對(duì)神秘的語(yǔ)言思辨的嘲諷:黑話毫無(wú)根據(jù)地以其純樸為榮,,很小心地不去回憶那一語(yǔ)言思辨,。黑話模糊了語(yǔ)言品味的“言外之意”和這個(gè)“言外之意”的自在存在之間的差異。偽善成了先驗(yàn),,此地此時(shí)所講的日常語(yǔ)言似乎成了神圣的語(yǔ)言,。

霍克海默(左)與阿多爾諾。兩人合著有《啟蒙的辯證法》(1947年),。
凡俗的語(yǔ)言只有遠(yuǎn)離神圣的聲音,而不是試圖模仿神圣的聲音,,才能夠接近神圣的語(yǔ)言,。黑話褻瀆性地逾越了這條規(guī)則,。當(dāng)它給經(jīng)驗(yàn)的詞語(yǔ)披上了靈韻,便嚴(yán)重夸大了哲學(xué)的普遍概念和觀念(例如存在概念),,以至于這些概念的本質(zhì)——亦即思維主體的中介作用——徹底消失于彩色涂料之下:這些術(shù)語(yǔ)裝扮成最具體的東西,,誘惑著我們,。先驗(yàn)和具體閃閃發(fā)光,。兩可是語(yǔ)言的某種姿態(tài)的媒介,這種姿態(tài)遭到了它所鐘愛(ài)的哲學(xué)的詛咒,。
然而,,浮夸不打自招地揭露了虛假。在長(zhǎng)期的分居之后,,某個(gè)人寫道,,他得到了生存論上的安全;需要停下來(lái)想一想,,才知道他說(shuō)的是他足夠謹(jǐn)慎地處理了他的財(cái)務(wù),。國(guó)際會(huì)議中心——不論這些會(huì)議有何用處——被稱為“照面之家”;看得見(jiàn)的房子,,“牢固地建基于大地上”,,被那些集會(huì)變成了圣地。也就是說(shuō),,房子高于會(huì)談,,因?yàn)樗鼈兲幱谏嬷摹⒒钌娜酥g,,盡管這些人正忙于會(huì)談,,而且只要他們不自殺,他們幾乎沒(méi)有任何超越生存的可能性,。
人和他的伙伴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比任何內(nèi)容都更重要,,為此目的,黑話滿足于青年運(yùn)動(dòng)那拙劣的共同體情結(jié),,它審查著事物,,不允許它們超出說(shuō)話者鼻子的可觸范圍或者超出人的能力。黑話把參與導(dǎo)向了固定的機(jī)構(gòu),并增強(qiáng)了最底層的說(shuō)話者的自尊:他們已經(jīng)很了不起了,,因?yàn)樗麄兊捏w內(nèi)“有人”在說(shuō)著話,,哪怕那個(gè)“有人”是“烏有”,。
偷偷地給非理性主義加熱
回蕩在黑話中的命令,,亦即“思想不應(yīng)太費(fèi)力”(因?yàn)榉駝t就要冒犯共同體)這一指令,也成為這些人高人一等的證明,。這就壓制了一個(gè)事實(shí),,也就是說(shuō),具有普遍性和客觀性的語(yǔ)言本身已經(jīng)否定了整體的人,,否定了正在講話的單個(gè)主體,。
語(yǔ)言的第一個(gè)代價(jià)正是個(gè)人的特殊存在。然而,,通過(guò)整體的人在講話而不是思想在講話的表象,,黑話這種“現(xiàn)成在手”的傳播方式就假裝出一副免遭殘暴的大眾傳播之傷害的模樣;恰恰是這一點(diǎn)才使它得到了人們的熱情迎接,。任何站在言語(yǔ)背后的人,,擺出一副那些詞語(yǔ)的樣子的人,都不會(huì)被人懷疑他此刻居心叵測(cè):他為別人說(shuō)話,,是為了向他們推銷什么東西,。一旦說(shuō)某個(gè)命題為“真”,那么“命題”一詞便終于獲得了它不在作案現(xiàn)場(chǎng)的證明,。通過(guò)它的特權(quán),,它想要讓那個(gè)“為別人”獲得一種自在的可靠性。在所有傳播存在之處,,這些比傳播更好,。

電影《安妮·霍爾》(1977)劇照,。
相關(guān)新聞
是護(hù)士,,更是“白衣戰(zhàn)士” | 新京報(bào)快評(píng)
2022-05-12 09:51:22新京報(bào)反家庭冷暴力,如何才能落到實(shí)處 | 新京報(bào)專欄
▲家庭成員之間的冷淡或漠視,,作為一種冷暴力,,后果不亞于身體侵害,,同樣不為法律所容忍
2022-03-27 18:51:00新京報(bào)在時(shí)代的考場(chǎng)書寫青春答卷 | 新京報(bào)社論
2022-06-07 00:11:16新京報(bào)疫情期間,,該如何給基層“減負(fù)”|新京報(bào)專欄
2022-04-24 19:51:14新京報(bào)打起精神來(lái),,防疫關(guān)鍵時(shí)刻不能懈怠 | 新京報(bào)社論
▲5月24日,豐臺(tái)區(qū)芳星園二區(qū)核酸檢測(cè)點(diǎn),,居民核酸采樣前進(jìn)行個(gè)人信息登記,,工作人員旁邊放置了電風(fēng)扇
2022-05-27 00:00:59新京報(bào)想方設(shè)法提振消費(fèi)信心,已刻不容緩 | 新京報(bào)專欄
2022-05-28 09:31:16新京報(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