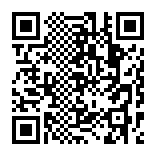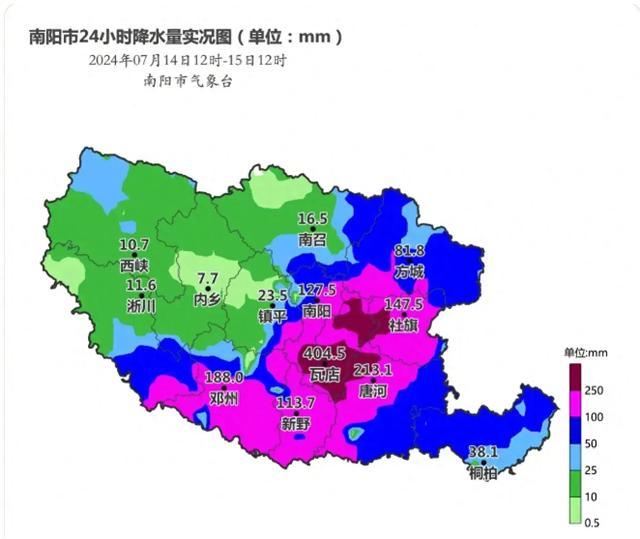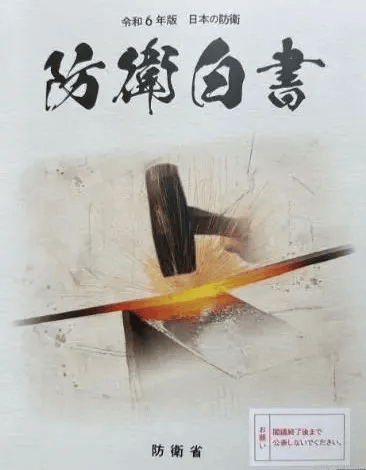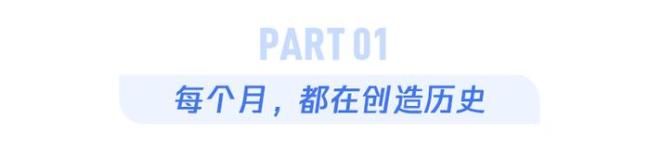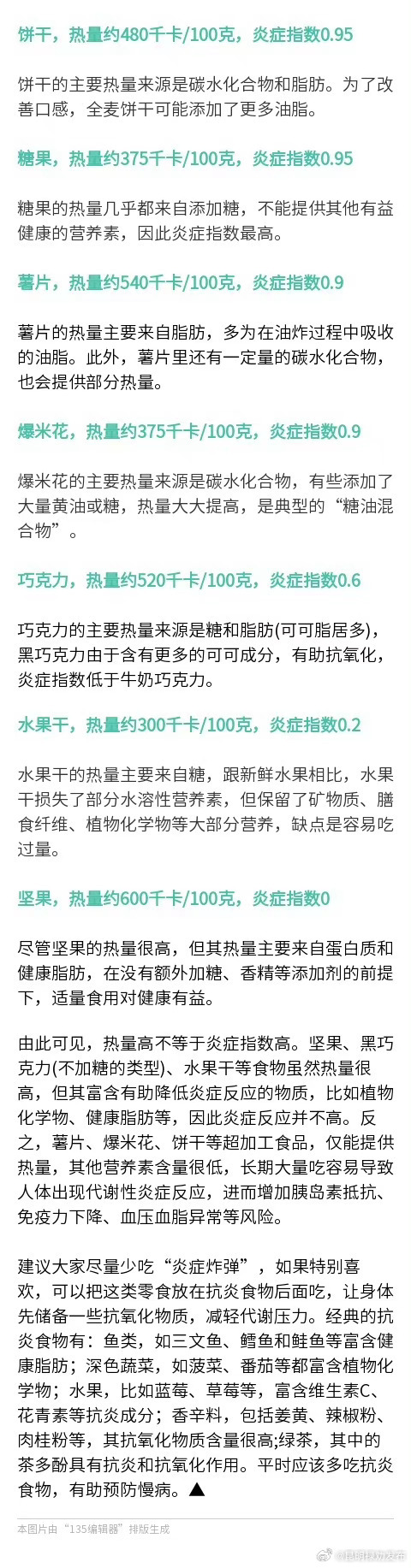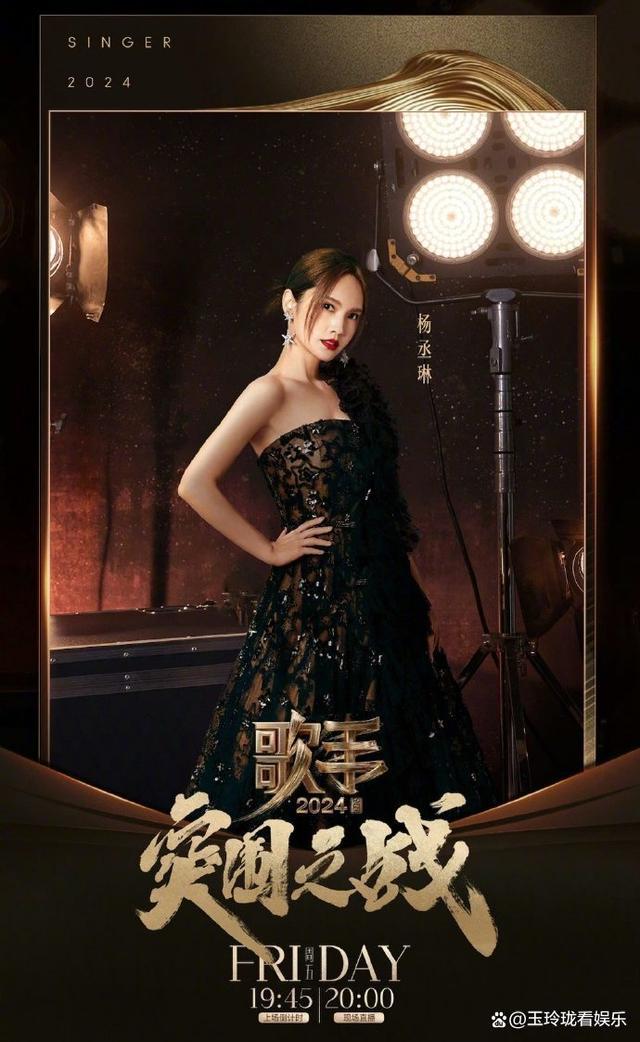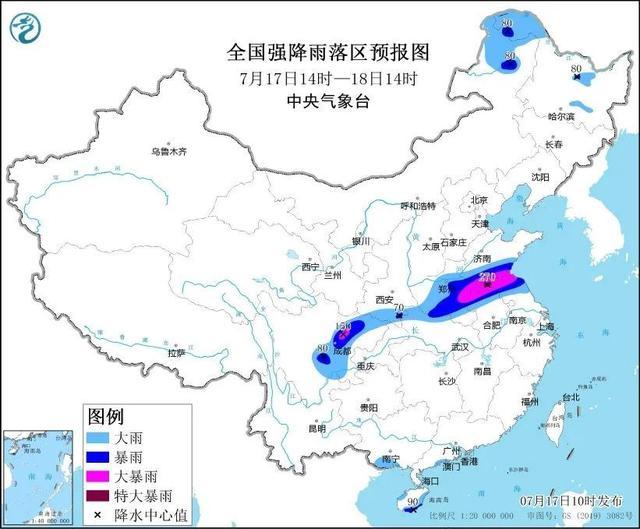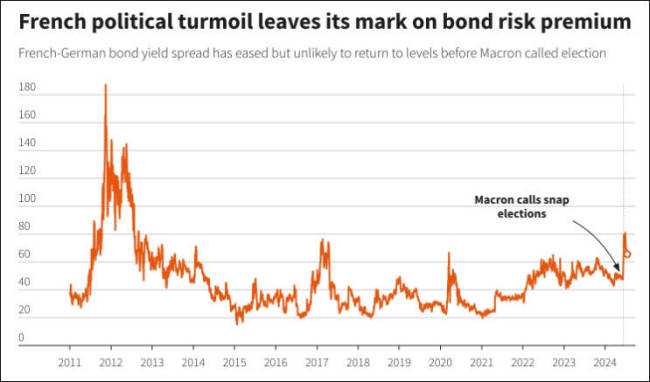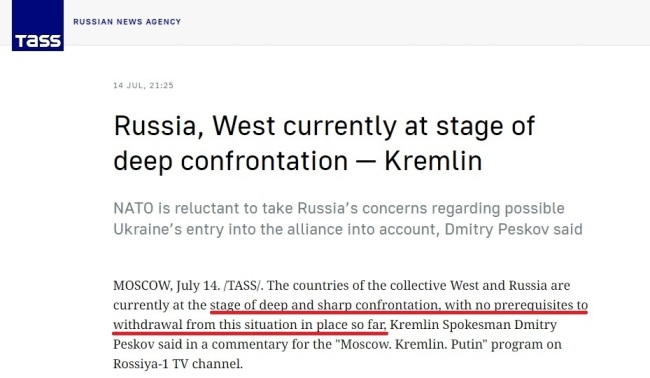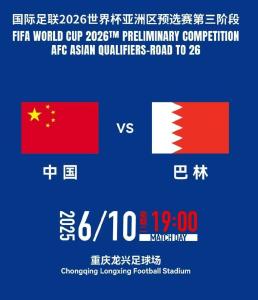學(xué)者黨成孝談《哈耶克論哈耶克》(4)
在另一觀念線索上,,隨著私有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建立得到確認(rèn)的個(gè)人自由觀念往往“把自發(fā)性和沒有強(qiáng)制看作是自己的精髓”,,故而“贊成有機(jī)的,、緩慢的和半意識(shí)的生長”(《自由秩序原理》第四章)。自發(fā)和建構(gòu)的矛盾,,在現(xiàn)代表現(xiàn)為組織的自然演化和契約論之間的差異,后者在“自然狀態(tài)”的假設(shè)之下以人為契約將個(gè)體捏合為國家,,也預(yù)設(shè)了共同體意志及其表達(dá)的優(yōu)先性,。而另一傳統(tǒng)下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則把對共同體優(yōu)先的否定表達(dá)為對個(gè)體激情的接納,,他們關(guān)心的是“人性中最普遍的原動(dòng)力——愛己(self-love),,是如何通過本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為目的的個(gè)人努力而被導(dǎo)向促進(jìn)公共利益上面去”(同前),。在復(fù)雜的社會(huì)交往脈絡(luò)中,,自利的個(gè)體行動(dòng)與群體層面非意圖結(jié)果間的參差,往往是秩序演化的應(yīng)有之義。就此而言,即便申述個(gè)人自由的思想家也并不完全在“盎格魯自由”之列。英倫的功利主義者如約翰·密爾以是否影響他人作為“群己權(quán)界”的劃定,,必然滑向國家權(quán)力的普遍介入,;以后果論證道德也將導(dǎo)致法律體系及其制度的完全重構(gòu),。其對自發(fā)秩序的破壞最終將反過來不可避免地?fù)p害作為土壤的個(gè)人自由,。
三
無可否認(rèn)的是,,盡管對二十世紀(jì)政經(jīng)實(shí)踐的反思只是這道觀念鐵幕的構(gòu)成性起點(diǎn),但它卻作為一種源頭性的經(jīng)驗(yàn)浸潤了哈耶克回溯性思考的方方面面。無論戰(zhàn)爭中的倫敦歲月,,還是戰(zhàn)后執(zhí)教于芝加哥大學(xué),,基于這種反思而對人之限度和個(gè)人自由脆弱性的覺察與警醒,使哈耶克試圖在異時(shí)異地同一切形式的相反實(shí)踐斗爭,。對理性突破限度的肯定,,必然會(huì)破壞理性得以滋長的自由環(huán)境,因此從思想史角度嘗試將個(gè)人自由脈絡(luò)與啟蒙的理性主義傳統(tǒng)完全撇清,,就成為捍衛(wèi)前者的重要奠基性工作,。
相關(guān)新聞
學(xué)者談美國的“選舉人團(tuán)”
2024-06-28 15:00:55學(xué)者談美國的“選舉人團(tuán)”學(xué)者談以色列為何不承認(rèn)巴勒斯坦國 深層原因剖析
2024-05-11 14:28:00學(xué)者談以色列為何不承認(rèn)巴勒斯坦國臺(tái)灣地區(qū)今日“大選”投票 選前“疑賴論”發(fā)酵,,美國學(xué)者官員密集發(fā)聲
2024-01-13 13:29:29臺(tái)灣地區(qū)今日“大選”投票「環(huán)時(shí)深度」外國學(xué)者談美對華恐懼“神經(jīng)質(zhì)”
2024-05-29 19:41:57美國專家稱美對華恐懼已經(jīng)失控駐巴西大使談所謂“產(chǎn)能過剩論” 駁斥雙標(biāo)言論
中國駐巴西大使祝青橋在5月16日的巴西著名財(cái)經(jīng)雜志《審視》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中國新能源汽車產(chǎn)能過剩論站得住腳嗎,?》
2024-05-19 11:03:35駐巴西大使談所謂“產(chǎn)能過剩論”清華學(xué)者閻琨談偏才怪才的培養(yǎng):重在個(gè)體甄別選拔
2024-06-18 14:51:30清華學(xué)者閻琨談偏才怪才的培養(yǎng)